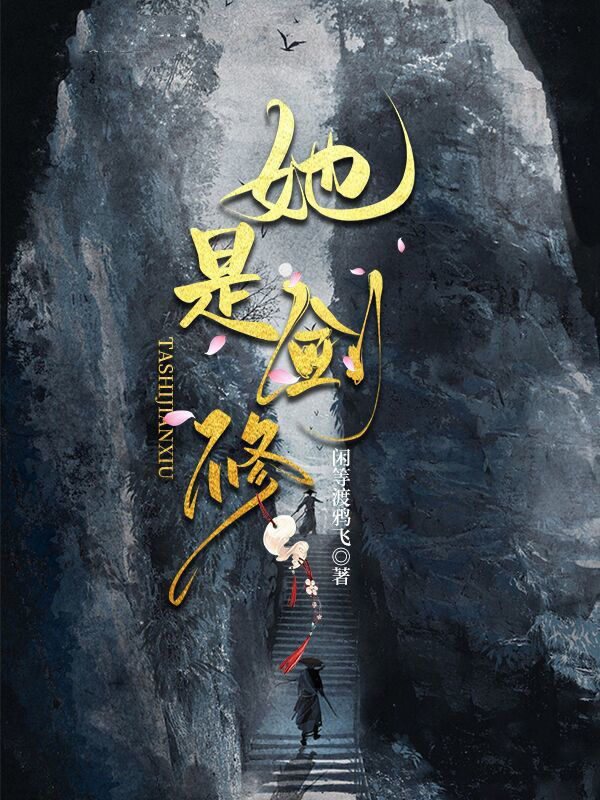随着夕陽徹底落下,夜幕降臨了,盛夏的夜晚在聲聲蟲鳴中顯得甯靜而悠遠。
月上柳稍頭的時候,燈火通明的驿站中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阿昕!”
蕭奕笑吟吟地對着被竹子帶進屋子的藍袍青年招了招手。
蕭奕的笑容、蕭奕的神情皆一如往昔。
然而,南宮昕卻無法像蕭奕這般平靜,距離他上次去南疆才不過兩年多,對他而言,似乎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仿如隔世。
南宮昕當然聽說了鎮南王府攻下百越、南涼和西夜的事,看着蕭奕和官語白的眼神難免有幾分複雜,别人也許會擔心鎮南王府北伐,但是南宮昕知道他的妹夫不會。
他所認識的蕭奕不屑這麼做!
“阿奕,侯爺。”南宮昕與二人見過禮後,就在二人身旁坐下。
蕭奕親自給南宮昕斟茶,語調親昵一如往日,似乎從未别離。
“阿昕,你來得正好,我還想着明天派人去請你過來一叙。”說着,蕭奕做了一個手勢,竹子便拿出一個畫軸,呈給了南宮昕,“這是阿玥特意囑咐我帶給你和六娘的。”
南宮昕帶着一絲狐疑地接過畫軸,然後打開,目光一下子就被畫紙上的畫吸引住了,移不開眼。
米黃色的宣紙上,畫着一個頭戴貓耳帽、身穿藍色小衣裳的奶娃娃,奶娃娃正抱着一隻胖乎乎的橘貓在地毯上打滾,笑得小嘴翹起,一雙如點漆的眼睛彎成了新月……
無論是這個奶娃娃,還是他懷中的橘貓都畫得是那麼生動,細膩,活靈活現。
這是妹妹畫的。
這畫中的奶娃娃似乎帶着一種神奇的渲染力,看得南宮昕的嘴角也不由得翹了起來,脫口道:“這……這是煜哥兒?”煜哥兒都這麼大了!他還沒親眼看過他的小外甥……
一看南宮昕癡癡地盯着手上的畫,蕭奕就知道自家的臭小子不費吹灰之力又收服了他舅舅。
這幅畫還是南宮玥知道他要來王都後特意畫的,就是想讓南宮昕和傅雲雁看看小蕭煜。
“阿昕,要不要去見見我家那個臭小子?”蕭奕看着南宮昕不答反問。
南宮昕怔了怔,擡頭看向了蕭奕,若有所思。阿奕是想讓自己“避”去南疆嗎?
蕭奕毫不躲避地與南宮昕四目直視,等于是肯定了南宮昕的疑問。
南宮昕卻是毫不遲疑地搖了搖頭,不疾不徐地說道:“阿奕,我要留在王都。”
南宮昕的表情溫和而堅定,頓了一下後,他繼續說道:“反正家裡的其他人都已經避去了江南,六娘有詠陽祖母護着,不會有事,所以我要留在王都助敬郡王一臂之力……”
皇帝雖然下了诏書立韓淩樊為太子,可是在場的衆人都知道皇帝早已非當年那個皇帝,太子就算立下,也可以廢。
他和韓淩樊既是君臣也是知交,哪怕前途再艱辛,他也不能就這麼甩手離開……
南宮昕看似性子溫和,卻自有他的堅持,就如同自己的阿玥一般。蕭奕的嘴角染上一絲笑意,他早就猜到南宮昕不會輕易離王都,倒也沒太意外,也沒打算強求。
蕭奕拍了拍南宮昕的肩膀,道:“阿昕,你既然心意已決,那我也不再勸你。但是‘君子不立于危牆之下’,你也要有所準備才行……”
跟着,蕭奕就把自己在王都中安插的人手和據地都一一告訴了南宮昕,最後叮囑道:“阿昕,将來若是有什麼意外,你就去王都南大街的鳳吟酒樓,那裡的掌櫃會護你們一家前往南疆!”
南宮昕深深地看着蕭奕,一陣心緒起伏,想道謝,卻又覺得一個“謝”字太過單薄。
他拿起了跟前的茶杯,将其中的溫茶水一飲而盡,與蕭奕相視一笑。
以茶代酒,一切盡在不言中……
夜漸漸深了,南宮昕在詠陽大公主府的護衛護送下悄然而來,又悄然而去,隻帶走了一個畫卷。
一彎新月在夜空中孤傲地俯視着衆生。
當銀月淡去、旭日初升時,驿站四周也蘇醒了過來,三千幽騎營立刻整裝待命,在蕭奕和官語白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地往西邊行去,一灰一白兩頭鷹在上方展翅翺翔。
守在驿站的數十名錦衣衛見蕭奕一行人往西山崗的方向絕塵而去,暗暗地松了口氣。
大部分人的心中都忍不住又一次浮現某個疑問——
難道說蕭奕和官語白不惜千裡迢迢北上,真的不是意指王都,僅僅是為了官如焰大将軍的骸骨?!
很快,錦衣衛中就有一人策馬而出,前往王都報訊。
這些事,蕭奕和官語白根本就毫不在意,帶着三千幽騎營直接來到了西山崗的山腳下。
原本空落寥寂的西山崗頓時因為他們的到來而變得有些擁擠起來,一片停在枝頭的黑鴉怪叫着驚起,被雙鷹追逐得狼狽而逃,讓這裡原本瘆人的氣氛變得活躍了不少。
三千幽騎營在山腳待命,官語白和蕭奕隻帶了一些官家舊部上山。
那些官家舊部無聲地往空中撒着一把把白色的紙錢,那些紙錢随着山風肆意飛舞着,就像這盛夏忽然下起了一場鵝毛大雪,飛飛揚揚……
四周的溫度似乎都驟然下降了不少。
這一路皆是沉默。
在這種凝重的氣氛中,每個人都不由得肅然,步履堅定地走在狹小的山道上。
就在一路沉默中,衆人來到了西山崗的山頂上,來到了官如焰的墓碑前。
上一次,蕭奕與南宮玥來到這裡為官如焰掃墓已經是四年前了,當年,呂文濯伏法後,官語白親自為官如焰以及這一整排的無字墓碑刻了字,無數王都以及周邊的百姓都聞訊前來祭拜官如焰……
彈指就四年了!
這些墓碑仍然如當年一般屹立在這裡,如當年般一塵不染,那一行行的刻字上的漆色鮮亮如往昔……
就仿佛歲月在這裡停滞了一般。
是啊,他們的歲月早就停滞不前了。
一行十數人就這麼靜靜地站在這些墓碑前,默默地懷念着埋在土下的這些故人。
死一般的沉寂蔓延開來,唯有那山風吹動枝葉發出的簌簌聲,仿佛那死者的哀歎聲……
聲聲不歇!
衆人的眼眶都紅了,濕潤了,每個人都強忍着其中的淚水……
反倒是官語白最為平靜,一雙眸子幽深得如暗夜,仿佛要把人的神魂給吸進去,一襲寬松的白衣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官語白忽然退後了一步,出聲道:“開始吧!”
三個字雲淡風輕,卻又似乎是用盡了他全身的力量……
小四、風行和其他官家舊部皆拿着鐵鍬、鐵鋤上前,沉重的墓碑被移去,黃土被一鍬接着一鍬地挖起……
官語白一眨不眨地看着,仿佛要把這一幕幕深刻地镌刻在心頭一般。
一鍬接着一鍬,一鋤接着一鋤,就像是把官語白身上好不容易愈合的傷疤再次挖開,把好不容易長好的骨頭再次打斷……
所有人都覺得心口發疼,發緊,仿佛這每一鍬、每一鋤都如重錘般敲打在他們的心口。
挖出的黃土越堆越多,一個黑色的棺椁在黃土之下漸漸地露出了輪廓,這是官如焰的棺椁。
幾個官家舊部挖掘的動作不自覺得慢了下來,眼眶再一次紅了,往昔的許許多多回憶在他們的腦海中閃過……
他們要帶着官大将軍的屍骨去與夫人團聚。
他們還要帶走官副将、劉副将、楊校尉他們的屍骨,不讓他們孤獨地留在王都這鬼地方!
山頂上的墳墓被一個接着一個地挖起,沾着泥土的棺椁被一個個地從墳墓中擡出,然後由這些舊部兩人扛一個,魚貫而下……
白色的紙錢又一把把地灑下了空中,把前路鋪成一片雪白色,天空不知何時陰沉了下來,讓人的心情更為壓抑。
一排排棺椁被放上了一輛輛闆車,用繩索加以固定,然後蕭奕一聲令下,這些棺椁就在三千幽騎營的護送下,原路返回驿站。
不遠處,又是一騎錦衣衛策馬往王都而去……
“世子爺……”一個幽騎營小将悄悄在蕭奕耳邊附耳禀了一句。
蕭奕嘲諷地勾唇,做了個手勢表示他知道了。
他随意地朝王都的方向看了一眼,眸中閃過一道銳利的精光。
希望皇上這一回也别讓他失望才行!
數千馬蹄聲隆隆而去,而那錦衣衛明明孤身一人卻仿佛是背後有人追趕似的策馬疾馳,以最快的速度趕回了王都……
半個時辰後,錦衣衛指揮使陸淮甯就親自進宮求見皇帝。
禦書房中,待陸淮甯禀明西山崗上發生的一切後,皇帝久久無法平靜下來。幾夜未能安眠,皇帝的眼窩深深地凹了下去,憔悴不堪。
錦衣衛傳來的每一個消息都隻是令皇帝越來越煩躁、忐忑、焦慮……
皇帝眉宇緊鎖,忍不住脫口問道:“他們就這麼回驿站了?”
就這麼帶着官如焰的棺椁回了驿站?
沒有任何其他的行動?
陸淮甯低下頭,恭聲稱“是”。
這時,一陣輕巧的步履聲傳來,韓淩賦親自捧着一盅藥茶走了過來,“父皇,您的安神茶。”
韓淩賦恭敬地将藥茶呈上,也讓皇帝猛地回過神來。
還是小三孝順!皇帝心中感慨地想着,腦海中不由響起昨晚韓淩賦和韓淩樊返回皇宮後的回禀,蕭奕說:“可惜了,皇上今日沒來!”
這句話反複地在皇帝的腦海中回響了一夜,一遍又一遍……
蕭奕和官語白到底想幹什麼?!
他們總不至于真的要他堂堂大裕皇帝親自出城去迎接他們倆吧?!
想着,皇帝就覺得荒謬。
可是,他們既然是為了官如焰的棺椁而來,如今都挖了棺椁,為什麼還不趕緊走人?!
他們到底在等什麼?!
難道說鎮南王有什麼話要蕭奕親口轉述給自己?
如果自己不去見蕭奕,蕭奕是不是就要想方設法進宮求見自己?!
皇帝越想越不安,霍地站起身來,在禦書房中來回走動着……
有道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自己必須盡快送走這兩個瘟神!
自己必須化被動為主動……
皇帝的步履終于停頓下來,眼中閃過一抹果決,出聲道:“陸淮甯,傳朕之命……”
皇帝的聲音回蕩在偌大的禦書房中,空氣随之變得凝重,一旁的韓淩賦的眼簾半垂,盯着禦案上那熱氣騰騰的藥茶,眸光閃爍……
一屋子的君臣父子各懷心思,讓這禦書房中的氣氛隐約又透着一絲詭異。
又是漫長的一日眨眼過去,次日一早,天色還蒙蒙亮,王都卻在一片喧嚣中驟然蘇醒了。
數千禦林軍浩浩蕩蕩地出動,封路的封路,随行的随行,護衛的護衛……
在一種毫無預警的狀況下,皇帝的禦駕出動了,整個王都為之震動。
那些普通的百姓當然不知道皇帝出行所為何事,而那些關注着朝堂、宮中的一舉一動的朝臣勳貴們卻是心知肚明皇帝此行為何……
鎮南王世子蕭奕和安逸侯官語白昨晚抵達了王都十裡外的驿站,皇帝竟然纡尊降貴地親往相見,這也算聞所未聞了。
各府的唏噓聲可傳不到皇帝的耳中,聲勢浩大的禦駕就這麼從南城門湧出,一路往東南郊的驿站而去……
一隻信鴿在碧空如洗的上空飛過,撲棱撲棱地在禦林軍的上方越過,卻沒有任何人在意。
随着旭日高升,天空越來越明亮通透了。
這一日,陽光明媚,然而這小小驿站中的驿丞心情卻怎麼也明媚不起來。
先是鎮南王世子和安逸侯來了,現在連皇帝也來了。
他們這種小人物本來一輩子恐怕也見不到皇帝一面,如今得見天顔,卻隻覺得膽戰心驚。
禦林軍和南疆軍不會打起來吧?!
倘若這裡變成了戰場,他們這種無名小卒怕是就要交代在這裡了吧?!
看着三千南疆軍與五千禦林軍形成兩個方陣遙遙對峙,幾個驿丞心裡隻打鼓,汗如雨下。
蕭奕和官語白姗姗來遲地從驿站中走出,自然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禦駕上的皇帝,以及随行在兩側的韓淩樊和韓淩賦。
君臣遙遙而望,皇帝目光幽深地瞪着蕭奕和官語白,右手緊緊地攥成了拳頭,若是可以,皇帝真想下令立刻将這兩個逆臣萬箭穿心!
偏偏他不能,隻能眼睜睜地看着這二人信步閑庭地朝他走近……直到雙方相距不到十丈的地方,陸淮甯上前一步,攔住了去路,一副“爾等不可驚擾到禦駕”的樣子。
蕭奕也沒有在上前,似笑非笑地看着不遠處的皇帝。
“皇上特意來相送,吾等真是受寵若驚。”蕭奕笑眯眯地朗聲道。
他臉上可沒有一絲所謂的“受寵若驚”,從他的言行舉止,更感受不到一點對天家的敬意。
哪怕是面對皇帝,他和官語白都沒有下跪,沒有行禮,沒有自稱“臣”。
很顯然,在他二人的心目中,他們已經不再是大裕的臣子。
皇帝的面色鐵青,一雙銳目死死地盯着蕭奕,隻覺得被蕭奕在衆目睽睽下一巴掌甩在了臉上,打得他臉上生疼。
蕭奕滿不在意,反正他被人記恨慣了,要是什麼都放在心上,豈不是要夜夜難眠!
蕭奕眼中帶着一抹毫不掩飾的譏诮,拔高嗓門繼續道:“皇上能親自來為官大将軍送靈,實在是有心了!”
為官如焰送靈?!皇帝傻眼了,誰說他來這裡是為了給官如焰送靈,官如焰不過一介罪臣,有什麼資格讓他堂堂大裕皇帝為他送靈!
皇帝的瞳孔中湧現一片驚濤駭浪,胸口的怒意幾乎就要爆發,卻見蕭奕那邊又有了動靜。
蕭奕随手做了一個手勢,他身後的一個青衣小厮就把三炷香遞向了陸淮甯,香煙袅袅……
這三炷香自然不是給陸淮甯的,而是給皇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