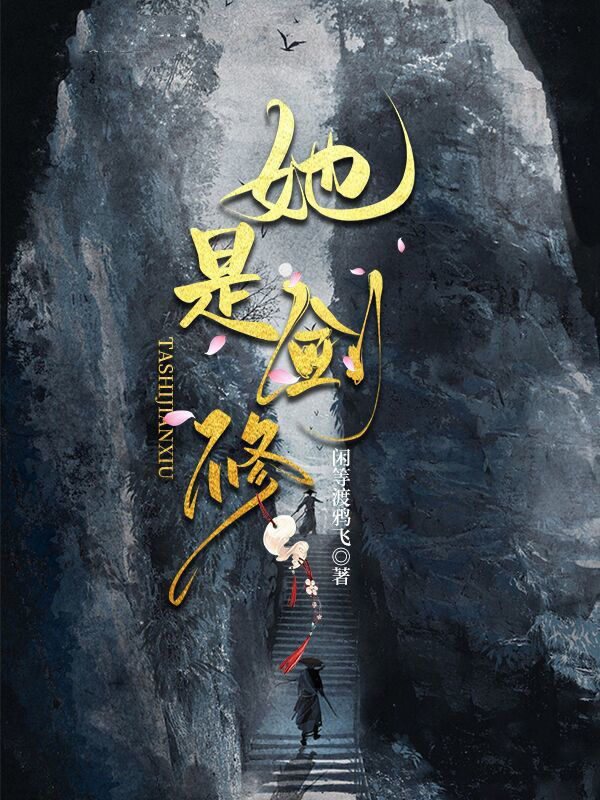辰時五刻,天地間依舊霧霭沉沉,這霧似乎越下越大了,比清晨還要濃些,田間地頭都變得影影綽綽,看不分明了。
杜家院門大敞,廚房的門窗全開着,三個小的,合力把廚房拾掇出一片空處。杜梅把每樣菜揀了一碗和飯端上了餐桌。找出一個瓦盆,四姐妹一字排開跪下,一邊燒紙錢,一邊輕聲禱告。
杜梅隻撿好事說了說,告訴她爹,她們有了弟弟,母親身體也好。并向她爹保證,她一定會照顧好母親和弟妹的。
杜世城心頭火下去了,人也恢複了七八成。但魏氏被他的急症吓着了,隻把他摁在床上,說什麼也不讓他去廚房,怕惹得他傷心難過。
許氏還在坐月子,不宜沖撞,所以也不能到廚房去。她隻得在自個屋裡默默念了一回,又哭了一場。
杜松倒是乖巧,也不睡覺,隻躺在包被裡瞪着黑烏烏的眼珠子看着許氏。許氏的奶~水比生前幾個孩子都好,杜松皺巴巴的皮膚已經被喂養地撐開了,抱在手上,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三房寂靜無聲,三金夫婦從公婆屋裡出來,就回自己屋了,杜傑和杜棗,影都沒露,早飯也沒在公中裡吃。
大房就更不要提了,一早上就闖了禍,這會兒倒安生了。周氏在屋裡假模假式地禱告,求個自己心安。
三摞子紙錢燃盡了,四姐妹挨個磕了頭。
倏然,一陣風自門外刮了進來,繞着四姐妹轉了一圈,溫柔地撩起她們的垂髫,發絲飛舞,四姐妹隻覺暖意撲面,如沐春風。眷念片刻,風裹挾起瓦盆裡的灰燼,散了出來,忽悠悠轉了一圈,又從門處消失了。
“大姐,我覺得是爹回來了!”杜桂握着杜梅的手,笑着流淚。
那風真的如同她們的父親平日裡對她們的溫柔愛撫,杜梅亦是霎時癡念。她被杜桂叫着,才恍然回神。杜櫻和杜桃雖比杜桂大,卻也早已紅了眼眶,傻愣愣地看着她。
“爹會永遠在天上看着我們,保佑我們的。”杜梅撈着三個小的抱住,她用小小的胸膛護衛着她的妹妹們。
忍不住哭了一場,四姐妹擦擦臉,心照不宣地不想被母親看出端倪。
“你們姊妹四個可看見你爹了?”許氏一見她們來,就急急地問。
“怎麼了?”杜梅問。三個小的不敢說,怕惹了母親的眼淚。
“你爹剛才肯定來過了。”許氏信誓旦旦地說。
看着四個女兒默不作聲,她着急:“真的,剛來了一陣暖風,我聞着是你爹身上煙葉子的味道。而且,杜松剛才突然咯咯地笑了!”
據說,小嬰孩是可以看見大人看不見的。許氏大概是思念過甚,又傷心難過,甯願相信二金真的會回來看他們孤兒寡母。
“娘,我們好好的,爹就放心了。”杜梅不知道怎麼安慰失去丈夫的母親,隻好抱着她。三個小的也乖乖地擁上來。
“嗯。”許氏抽了下鼻子,她這做娘的還要孩子們擔心,真是沒用的很。
她張開臂膀一把摟着她們,與她們每個人的頭靠靠:“娘沒事,等娘出了月子,就多接點繡活,你們爺奶就不會這麼為難你們了。”
杜梅忙了一早上,這會兒想了想,覺得阿爺突然吐血實在蹊跷。她們從大房走的時候,阿爺還好端端地坐着呢。怎麼一盞茶的工夫就吐血了?
她隻把這事放在心裡,不想給母親添堵,就沒有往外說了。
四姐妹在母親身邊膩了一會兒,就回到廚房收拾。
二金的喪事剛好在臘月裡,恰逢過年。時間上倉促,很多事情都從簡了。今天是頭七,卻是要把許多事一起了了。所以今天,杜世城請了杜懷炳來家吃飯,還請了一個在喪禮上幫忙寫白榜的老童生杜斐鎬。
杜斐鎬年過五十了,連考了二十多年秀才,家中藏書汗牛充棟,卻不知是運氣不濟,還是無緣伯樂,一直差之分毫,名落孫山。
他家裡原是個富戶,家産田地在杜家溝也是排的上号的,隻是這一房财旺人不旺,三代單傳到了杜斐鎬這輩。偏他是個屬驢的,發誓不得功名不娶妻。這原是酸文人恃才傲物的一種混賬說法,沒想到他硬是鑽了牛角尖。
父母也曾好言勸慰,要他先成家後立業,他自是牛心左性聽不進。待年紀愈大,父母也是無法了,恐他子嗣無望,甚至是求他娶親,生個一男半女。可媒婆換了好幾個,也沒說上一門親,高不成低不就,竟白白荒廢了光陰。
不久,兩位老人陸續下世,他又不是個善于經營管理的,今日不管明日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家裡沒個商量計較的,家産田地不知被近族遠親诓騙了多少去。
直到四十歲上,他才突然幡然醒悟,捂緊了錢袋子。這時,他也就僅剩3畝水田和一處老宅了。他又不會種田,隻平日裡幫着村裡做做寫寫算算的事。他嚴謹細緻,算盤打得尤其好,紅白喜事,大家夥都請他幫襯,一個人的日子倒也過得逍遙自在。
他對科舉應試完全喪失了信心,卻又癡迷上了另一件事。他某日早上醒來,發宏願要寫一本曠世奇書。這一寫就是七八年,書稿堆了一屋子。
看了他書的人都說他的腦殼子壞了,人怎麼能坐在大鐵鳥的肚子裡飛?女人怎麼能不穿長裙,露胳膊露腿出門?遠隔千山萬水的兩個人怎麼能聽見彼此的聲音?還有什麼不用墨水就能寫字的筆,不添油就亮的燈?沒人信他寫的一千年後的離奇故事,隻當是個笑談,傳得十裡八鄉人人皆知。
他倒也不惱,隻在他爹娘留下的老宅上挂了個大匾,親題三個鬥大的字:廢稿齋。村裡人叫順了嘴,從此,杜斐鎬成了杜廢稿了。
到了飯點,杜懷炳和杜斐鎬來了,杜世城自覺家醜不能外揚,掙紮着起來招待。杜懷炳見他臉色不善,隻以為他還為昨日的事氣惱,不免又開解了一番。
杜梅把菜略熱熱,一樣樣端上來,魏氏割了一小塊臘肉拿到廚房,杜梅做了臘肉大白菜,又加炒了雪裡蕻肉絲,湊齊了八菜一湯。
杜世城又讓燙了一壺燒酒,叫出三金陪着一起吃飯。大金傷了,出了昨兒的事,也沒臉面出來陪客。大房的三個小子,撇了輩分不說,也是上不得台面,杜世城就沒喊。
堂屋八仙桌上,四個人吃一桌子菜,已是異常豐盛了。杜懷炳是長輩,三人輪番敬酒。杜家父子二人又敬了費稿,杜世城把感謝的話說了一籮筐。費稿還有着文人的傻氣,和三金倒也投緣,說到二金不禁唏噓了一回。
杜世城精神不濟,不過兩三杯,就有了醉意。魏氏一直在堂屋外守着,見狀,忙沏了酽酽的茶來,杜世城就以茶代酒作陪。
杜家其他的人都在廚房裡吃飯,桌上是一大盆青菜豆腐,一大碟雪裡蕻,肉絲太少,都緊着堂屋那桌上了,不過沾着肉腥味,味道也好過清炒,還有一盆白菜湯,也泛着油花兒,聞着都香。另外就是祭奠二金用的,裝在碗裡的菜。
謝氏帶着杜傑和杜棗來了,周氏和杜栓杜樁也來了,大金和杜柱躺着,等着送飯。周氏等不及地裝了兩碗飯,又把各種菜夾了碼在上頭,她兩手各端着堆得高高的飯菜,胳膊窩裡還夾着兩雙筷子,急急地送到房裡。
等周氏回來,碗裡的菜已經沒有了,豆腐也沒有了,雪裡蕻裡的肉絲兒更是挑得一根不剩。她想發飙,但想到今天日子特殊,就焉了,不敢多說話,隻管扒飯。今天是純粳米飯,又香又軟,沒菜都能空口吃兩碗。
杜梅今天給許氏汆了碗鲫魚豆腐湯,揀了點雷蘑雞蛋,早早打發杜櫻送了。也不和這幫惡鬼争食,淘氣。
費稿一年到頭,難得吃這麼好的席面,滿桌的菜不是啥稀罕物,就是色彩和滋味與其他人家的大不相同,他由衷贊歎。說着說着,又拐到說自己寫的書上的美食,三金倒是好奇的緊,說定過年空閑時,必要登門一觀。費稿自是歡喜異常,恨不得立時扯了三金就去。
他們年輕一輩聊得投機,推杯換盞,不亦樂乎。杜世城就撇過頭和杜懷炳咬耳朵:“老叔,過了年,初八,您上我家來一趟呗。”
“啥事?”杜懷炳疑惑地問。鄉下人一般要過了正月十五小年才算真正過完了年。一年忙到頭,沒有特别重要的事,正月裡是不會勞煩旁人的。
“沒啥子事,到時請您去。”杜世城往煙鍋裡填煙絲。
“你莫要介懷,過幾日,熱鬧勁過了就好了。”杜懷炳還認為是杜世城抹不開面子,受不了村人的指指點點。
“嗯。”杜世城用火折子點着了煙絲,嘴用力一嘬,煙氣就從嘴裡冒了出來。
“老叔,您來一口?”杜世城讓讓煙杆。
“我不好這個,太沖。我勸你,也少抽點吧,對身體不好。”杜懷炳拿眼看看杜世城,這不過一日的光景,人怎麼跟剝肉削骨似的,背都有點佝偻了。
酒酣耳熱,杜梅又來上了飯,費稿知是眼前的姑娘做的菜,不禁多看了她兩眼。還完全是個孩子,瘦削單薄,唯那雙杏眼,晶瑩澄明,宛如暗夜裡的漫天星鬥閃閃發光。
吃罷飯,又上了茶,完全是最高規格的款待。在吃食匮乏的年月,能弄一桌像樣的酒菜請客吃飯就是對他人最好的感謝了。
二金的喪事,到這兒就算是完滿結束了。
杜家接着就要忙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