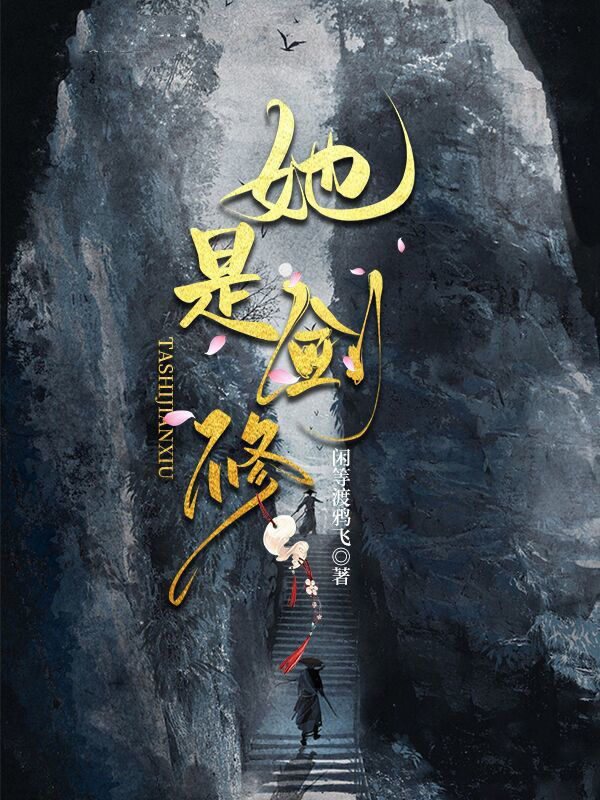等喬大夫人回到喬宅時已經是半個多時辰後了,她的一雙兒女都在正院的堂屋裡等着她,一見她歸來,兩人都是急切地迎了上來。
喬申宇身穿一件湖色織金錦袍,一頭烏發以一方白玉扣束得高高,端的是器宇軒昂;喬若蘭着一身水紅撒虞美人花亮緞粉紫鑲邊偏襟長褙子,鬓角的石榴珠花随着她款款走來微微顫動,優雅清麗。
每每看着這雙出色的兒女,喬大夫人就覺得老懷安慰。丈夫如此不成器,她能依靠的也隻有這一雙兒女了。
“母親,”喬申宇行了禮後,就迫不及待地追問道,“舅父他怎麼說?”他目光灼灼地盯着喬大夫人。
喬大夫人瞥了喬申宇一眼,沒有立刻回答,走了進去,直到在上首的太師椅上坐下,這才慢吞吞地颔首道:“我親自出馬,你舅父能不答應嗎?”
“那是自然。”喬申宇殷勤的為喬大夫人揉肩,“舅父他一向與母親您最親近了。”
喬大夫人拍了拍兒子的手,諄諄叮囑道:“宇哥兒,上一次西南撫民的事終究是惹得你舅父不快,這一次我也是好說歹說才讓你舅父點頭應了。宇哥兒,這一趟差事你可要争氣了。讓你舅父看看你的本事!”
“母親,您就放心吧。”喬申宇自信地昂首挺胸,“您還信不過兒子嗎?”
喬大夫人含笑地看着兒子,表情十分慈愛:“宇哥兒,娘就等着你掙個軍功回來。”把那個田得韬狠狠地踩下去!
喬申宇意氣風發,似乎已經看到自己錦衣還鄉的那一日,抱拳道:“母親,那我就先下去準備準備了。”
喬申宇很快退下了,一旁的喬若蘭已經憋了好一會兒了。
見哥哥走遠,她咬了咬下唇,心急如焚地問:“母親,他……他可曾……”她局促地扭着帕子,面泛桃花,眸中波光流轉,那唇角含情的樣子分明就是動了芳心。
哎,喬大夫人心底暗暗歎氣,吾家有女初成長,女兒看來真的對安逸侯動心了。
喬大夫人猶豫了一下,還是答道:“我問過你舅父了,安逸侯還不曾娶親。”這件事她就算想瞞,恐怕也瞞不住。
聞言,喬若蘭欣喜若狂,眸中綻放出一種令人炫目的異彩,嘴角不由翹起,心跳如小鹿般亂撞,浮想聯翩。
“蘭姐兒,”喬大夫人卻是皺緊眉頭,柔聲勸道,“你聽娘一句,娘看這安逸侯實在是不妥,他雖然位高權重,但是一看就身子骨不好……”往後閨房之中也會少了不少樂趣,更何況,若是一旦英年早逝,即便是生前多麼風光,留下孤兒寡母又能如何?!“蘭姐兒,娘是為你好。娘已經打聽過了,那傅三公子這次立了大功,又是皇上的表外甥,将來前途必不可限量,封侯拜相也是指日可待……”
可還沒等喬大夫人把話說完,喬若蘭就霍地站起身來,臉上透出一絲不耐煩,福身道:“娘,哥哥過幾日就要出發,想必您瑣事繁忙,有不少事物要為哥哥準備,女兒就不打攪您了。”說完,喬若蘭頭也不回地就走了。
喬大夫人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一股心火直沖腦門。這若是别人敢如此對她,喬大夫人早就翻臉了。偏偏是自己的女兒!
女兒自小聽話,才學出衆,就沒讓自己操過心,沒想到母女倆竟然在婚事上出現了這麼大的分歧!
喬大夫人胸膛一陣劇烈的起伏,忍不住對着一旁的胡嬷嬷埋怨道:“老話說的真是不錯,兒女是債,無債不來啊!”
胡嬷嬷忙安慰道:“夫人,安逸侯爺是姑娘的救命恩人,也難怪姑娘她……”
喬大夫人本來也對安逸侯頗為感激,可是這點感激早在喬若蘭的執迷不悟下消失殆盡,冷聲道:“也不知道那安逸侯是對蘭姐兒下了什麼蠱了。”女兒真是被他給迷了心竅!
胡嬷嬷在一旁賠笑,卻不敢答應。
喬大夫人捏了捏帕子,蹙着眉頭又道:“不行,我要趕緊把蘭姐兒的婚事定下才行!”
胡嬷嬷提醒道:“夫人,可是前方戰事還未結束,也不知道傅三公子何時才能回來……”
經胡嬷嬷這麼一提,喬大夫人不禁懊惱了起來,道:“剛才我應該問問王爺,傅三公子何時回來才是。”傅三公子如此佳婿,可不能讓蕭霏給搶走了。
不過此事終歸還是要等傅雲鶴回來才能有所作為,當下,她還是得先幫兒子準備出門的行李才是。
喬大夫人親自帶人跑去了喬申宇那裡,幫着整理了東西,又吩咐丫鬟、婆子備這備那,忙了近一個時辰,才把這些瑣事理了個七七八八。
等她回到自己的屋子,喝上熱茶緩了一口氣後,她才想起還要和喬興耀說說兒子要去惠陵城的事。
“紫蘇,去看看老爺回來沒?”喬大夫人轉頭吩咐道。
一身藍綠色褙子的圓臉丫鬟頓時身子一縮,眼神閃爍了一下,屈膝禀道:“夫人,老爺……老爺去了餘姨娘那裡。”那餘姨娘就是當初喬興耀養在金魚巷的外室,自從過門後,就深受喬興耀寵愛,一個月有一大半的日子歇在餘姨娘那裡。
“這個狐媚子!”喬大夫人順手就把手中的茶盅摔了出去,瓷片飛濺,滾燙的茶水灑了一地……
喬宅的雞飛狗跳暫且不提。
自從前方傳來大捷後,想要把自家孩子送去惠陵城蹭個軍功的人家不在少數,一時間,駱越城的各府邸都忙活了開來,托關系走人情,很是熱鬧……
當三日後喬申宇趕到駱越城大營的時候,就在随行的隊伍中,看到了兩張熟悉的面孔。
喬申宇的面色僵了一瞬,若無其事地與兩人打了招呼:“于公子,常公子!”
那兩人一人是于将軍府的四公子于修凡,另一人是常将軍府的五公子常懷熙。很顯然,這兩人是想去惠陵城那裡蹭軍功的,真無恥!自己絕不能被他們給比下去了!
喬申宇在心裡暗暗發誓。
衆人心底究竟怎麼想且不提,但表面上都是和樂融融。
不多時,李校尉到了,看到隊伍裡多了三四輛馬車還都是這些公子哥的私物,當下就怒了,勒令每人隻許攜帶一個包裹的行李,不然就别去了。
于是,馬車全都被留了下來,三人隻帶了幾件換洗的衣裳就匆匆跟着上路了。
李校尉率領辎重營浩浩蕩蕩地出發。
當他們抵達惠陵城時,又是過了數日,這一路舟車勞頓,喬申宇本以為終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沒想到李校尉從司徒守備處得了蕭奕的軍令,又要火速趕去雁定城,喬申宇當然也隻能跟着他們馬不停蹄地趕路。
一行人等終于在次日太陽西下的時候趕到了雁定城。
一聽說他們是來送糧草的,城門守兵核對了令牌,就立刻大開城門相迎。
“李校尉,”守正激動地說道,“千盼萬盼總算把您給盼來了。那些該死的南涼人占了雁定城後又是屠城又是搶掠,現在城中的百姓正等着您帶來的這批糧草救急呢……”
那段黑暗的日子,百姓們簡直苦不堪言,雖說世子爺打下雁定城後也命人送了些糧草過來,可那些糧草都是南疆軍和惠陵城那邊緊衣縮食硬省下來的,也隻能勉強維持個幾日……還好,終于有糧草來了!看到這些糧草,守正的心裡一陣慶幸,雁定城總算是熬過來了!
正事要緊,李校尉與守正沒說幾句就進城了,喬申宇策馬跟在李校尉的身後,有些漫不經心的打量着四周,雁定城蕭條死寂,散發着一種死氣沉沉的感覺。
昨日,喬申宇見惠陵城除了進出城守備森嚴,城中其他事務均是井然有序,就以為雁定城也是差不多,卻沒想到雁定城竟然是這副蕭條的樣子,十室九空,不少房屋都是牆殘瓦破,牆上、地上還留有暗紅色的血迹,那種若有似無的血腥味萦繞在鼻尖。
喬申宇不太舒服地幹咳一聲,在馬背上稍微調整了一下姿勢,隻覺得如坐針氈。若非是為了軍功,他早就待不下去了。
一行人等很快來到了守備府外,士兵們在府外待命,而李校尉和三位年輕公子則被迎進了守備府中。
總算可以休息了。喬申宇懶洋洋地打了個哈欠,暗暗松了一口氣。
“李校尉,世子爺正在書房等您,請随小的來。”一個士兵急忙領着李校尉去了外書房。
喬申宇想着自己怎麼說也是蕭奕的表兄,就也想跟着去打聲招呼,誰想,一個千總模樣的男子攔住了他,抱拳道:“喬公子,常公子,于公子,雁定城現在百廢待興,正是需要人手的時候,世子爺得知三位公子前來,特命在下來給三位傳軍令。”
喬申宇怔了怔,沒想到這還沒喘上一口氣,蕭奕的軍令就來了。這也太急了些吧?雖說他是來蹭軍功的,可一路跋涉,也想先休息個幾日再說……
于修凡迫不及待地問道:“大哥……咳,我是說,不知世子爺有何吩咐?”
一旁的常懷熙飛快地看了于修凡一眼,不動聲色。他也是在駱越城長大的,自然知道如于修凡這般有名的纨绔們從前好些都是跟着世子爺混的,稱兄道弟,以世子爺馬首是瞻。而這喬申宇又是蕭奕的表兄,也就是說三人中唯有他一人和世子爺無親無故。
景千總正色道:“三位公子,當日攻城時,我軍和南涼人皆有死傷,許多屍體分布在城裡城外,若是不及時處理,屍體的腐化容易會污染水源,并導緻疫病流行。世子爺已經命衆将士、全城百姓在城中搜索了數日,把城中的屍體基本都清理焚燒了。現在正在清理城外的屍體,此事就擾煩三位公子了。”
清理、焚燒屍體?!
于修凡的嘴角抽了一下,俊臉也差點垮了下來,心道:大哥也真是不講情面啊!……沒辦法,大哥的命令,再慘也要幹……其實,焚燒屍體雖然有些惡心,卻是再輕松不過的差事。于修凡的心裡有些發毛,隻能不停地安慰自己。
常懷熙的臉色也不太好看,一股濁氣悶在了胸口,差點就要脫口而出:憑什麼?!
自家好歹是三代将門,自祖父一代起,就在老王爺麾下效力的。世子爺給他如此下賤的活,莫不是要故意折辱自己?
常懷熙握了握拳頭,終究什麼也沒說,不着痕迹地觀察着于修凡和喬申宇。
喬申宇整張臉都僵住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臉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掩不住眼中的嫌惡。
“這位兄台,”喬申宇抱拳對那千總道,“可否讓我先見一見奕……世子爺?”他琢磨着等見了蕭奕,再讓他給自己換一個差事就是!
誰想,剛才還和顔悅色的景千總瞬間就變臉了,一雙單眼皮的細眼睛殺氣四射,四周的溫度驟然直降。
“喬公子,”景千總的聲音冷得幾乎要掉冰渣子,“在下剛才說的這可是世子爺的軍令!喬公子莫不是要違抗軍令?”
違抗軍令?!喬申宇瞳孔猛地一縮,抗軍令者杖,上一次,因為西南撫民的事,他足足領了三十軍棍,被打得皮開肉綻,在榻上躺了一月有餘。
喬申宇心有餘悸地幹笑了一聲,連忙改口道:“怎麼會呢?!我怎麼會違抗軍令呢。”
于修凡暗暗地憋着笑,看着這位喬公子雖然是自家大哥蕭奕的表哥,卻對大哥的心性不太了解,大哥平日雖然愛玩鬧,但是做起正事來,卻是說一不二。偏偏這喬申宇非要往刀口上撞!可憐可歎!
常懷熙半垂眼眸,眼中閃過一抹戾芒。世子爺估計是想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吧?哼,自己見招拆招便是!
景長總沒再理會喬申宇,直接說道:“三位公子,請随在下來吧……”
于修凡和常懷熙先後跟了上去,喬申宇雖然滿腹不甘,但咬了咬還是邁開了這一步。
景千總親自帶着三人從南城門出了城,這時,天色已經一片昏黃,隻有西邊的天空還留下一抹赤紅。
城外的一片空地上,已經搭建了一個巨大的木頭高台。
遠遠地,正好看到一隊三人的士兵護送這一輛闆式馬車往這邊而來。一行人越來越近,可以隐約地看到那輛闆式馬車堆滿了三五具屍體,一種濃重的屍臭味飄蕩過來……
涼涼的夜風一吹,那惡臭便迎面而來,彌漫在四周,讓人惡心作嘔。
喬申宇臉色慘白如紙,胃部一陣翻騰,差點沒吐出來。
“哒哒哒……”
四周萬籁俱寂,隻剩下馬車前進時馬蹄聲和車轱辘滾動發出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那幾個士兵在千總他們跟前停下,帶隊的伍長上前禀道:“禀千總,方圓一裡的屍體已經清掃完畢,是否……”
話語間,闆式馬車停在了後方,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具具慘不忍睹的屍體堆砌其上,鮮血淋漓,南疆天熱,屍體大部分已經腐爛,可以清楚地看到衣物和血肉間無數白生生的蛆蟲蠕動着,四周更是蒼蠅雲集,發出“嗡嗡嗡”的聲響。
喬申宇兩耳嗡嗡,什麼也聽不到了。
“嘔——”
他再也抑制不住惡心,轉過身對着一旁的草叢瘋狂地嘔吐起來……
看着喬申宇狂吐不止,常懷熙眼中閃過一抹輕蔑,強壓住心口的惡心感。
“嘔……嘔……”
一時間,隻聽喬申宇的嘔吐聲在空中環繞不去。
不一會兒,守備府中的蕭奕就得知了發生在城門口的事。
“……那個喬公子就連婦孺都不如。”景千總說道,“依末将看,他撐不了幾日就要來向您告辭了。”這幾日來,雁定城裡可是有不少老弱婦孺幫着一起打掃城裡的屍體,誰像那喬公子這般嬌氣的,“其他兩位公子暫且看來還好。”就是不知道真幹起來後會如何。
蕭奕嘴角勾出一個似笑非笑,走到了窗邊,往南邊的天空遠眺。
以他的距離和角度自然看不到城門外,卻能看到滾滾的白煙騰起,瘋狂地湧向夜空……
想必是城外又開始焚屍了……
自從他入駐雁定城後,基本上每晚的這個時候都要進行焚屍,找到的屍體數以千計,大部分都無法辨别身份,更沒有時間去辨别身份,屍體必須盡快地焚燒處理!
這就是戰争,殘酷而無奈。
蕭奕仰首盯着夜空好一會兒,才道:“不必理會他們,就算誰想回去也得給本世子把事情做完了!”
喬申宇、于修凡和常懷熙一來,蕭奕就得了消息。很顯然,這三人是被他們家裡送來這裡蹭點軍功的。
蕭奕當然明白這種事情是怎麼也避不開的,但是,想要軍功可以,總要有所付出吧。無論是于修凡也好,喬申宇和常懷熙也罷,隻要他們有本事,他是來者不拒!
這城裡,很多事情都等着人來做。
“是,世子爺。”景千總抱拳領命,恭敬地退下去了。
蕭奕又在窗邊靜立片刻後,轉身來到書案後坐下,處理起公務來。
每次從敵人手中收複一個城池,代表的不是結束,而是一個艱辛的開始。
雁定城原來的知府、守備早已經在城破時犧牲了,蕭奕新近提拔了麾下的一位立了功的正五品武德将軍為雁定城的守備,但是知府的職位卻需要等朝廷的批文,等新的知府上任恐怕還需要一段時日。如今城中的瑣事都需要由他來暫時處理。
修繕城牆、重整戶籍田地、清點庫房糧草、重新任命兩城官員、處置南涼降兵……大大小小的事務把蕭奕忙得焦頭爛額,隻能安慰自己等小白來了就好了。
這一晚,等蕭奕忙完以後,已經是二更天了。
看着天色不早,守在書房外的竹子終于忍不住進屋勸了一句:“世子爺,您該歇下了……”說完,他又補充了一句,“您要是累壞了身子,世子妃會擔心的。”
蕭奕沒理會他,奮筆疾書,一鼓作氣地寫了滿滿的兩張紙後,方才歇筆,遞給竹子說:“快去寄給世子妃!”一雙漂亮的桃花眼在燭光中閃閃發亮。
竹子不用看信,也可以猜到自家世子爺估計又在信裡跟世子妃撒嬌了。他接下信紙,笑吟吟地應了一聲,步履輕快地下去了。
想着他的臭丫頭,蕭奕一夜好眠。次日一早,他照例是聞雞起舞,打了一套拳,又沐浴更衣後,方才辰時出頭。
跟着,他就在一衆将領的環繞下巡視起雁定城的城防。
經過過去幾日的修繕,不少城牆上的缺口已經修補上,新舊石磚的顔色有着顯著差異,就像是一件經過反複修補的衣裳般,透着一種劫後餘生的滄桑感。
衆人沿着城牆往前走,沒一會兒,就看到不少身穿铠甲的守兵在修繕城牆,幾人搭磚,幾人砌泥,一些百姓也過來幫忙,不時發出铛铛的敲打聲。
李守備一邊走,一邊彙報道:“世子爺,那日攻城時,投石車破壞了不少城牆,修繕了數日,還有至少一半沒來得及修補,恐怕要再加些人手。磚塊方面,末将打算在城中找幾棟無人的宅子先拆了它們的圍牆拿來救急。”
蕭奕看向了景千總:“你那邊能調出人手嗎?”
景千總忙回道:“世子爺,屍體已經清理得差不多,再過兩日,可以再調一兩百人過來修繕城牆。”
李守備沉吟一下,又道:“如此,想必五天内應該就可以修繕好城牆了。”
話語間,城門出現在了衆人的視野中,隻見城門附近排了兩支長長的隊伍,百姓們一個個都衣衫褴褛,身形伛偻,一眼望去,大部分都是老弱傷殘。
李守備見蕭奕的目光朝那邊看去,就解釋道:“世子爺,昨日糧草送來了,所以末将清點完就立刻命人開始分發米糧。”
當初,南涼人在雁定城屠城三日,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殺害了城中大部分的青壯年,隻留下這些老弱傷殘為他們所驅使,城中的不少婦女更是遭受了慘無人道的傷害,不堪羞辱,自盡而亡。
每每看到這些可憐的百姓,士兵們都是義憤填膺,感同身受。
留着一把大胡子的鄭參将憤憤道:“還是太便宜那些南涼人了!”
“沒錯!”傅雲鶴扼腕地說道,“若非咱們的神臂弩太少,那一日也不至于讓那個伊卡邏給逃了!……大哥,這神臂弩實在是神兵利器,我們多備一些吧。”說着,他目光灼灼地望着蕭奕。
在收複雁定城、永嘉城的兩戰中,神臂營和神臂弩都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蕭奕也想擴大編制,可問題是,他沒銀子了!這支三千人的神臂營幾乎把臭丫頭封地的食邑都用光了。
可惜,衆将士們卻并不知情,神臂弩的威力他們可都是看在眼裡的,因而傅雲鶴這麼一說,便是連聲響應。
“若是再組建兩個神臂營,一定把那些該死的南涼狗打得屁滾尿流!”鄭參将接口道,聲音不自覺地拔高,目光正好對上了前方一個三四歲的小男童。
男童一雙烏黑的眼瞳瞪得圓圓的,小嘴微張,似乎是受到了驚吓,眨眼間,眼眶中已經含滿了淚水……
牽着男童右手的老婦人立刻注意到孩子的異狀,俯首看向她,擔心地問道:“黑子,你怎麼了?”
男童另一隻手緊緊地拉住了老婦的裙裾,嘴唇癟了癟,仿佛下一瞬就要哭出來了。
鄭參将渾身僵硬,他根本什麼也沒做好不好。
一旁的傅雲鶴辛苦地憋着笑,不客氣地對着鄭參将擠眉弄眼,仿佛在說,誰讓你長得兇,還在外面吓人呢!
------題外話------
眼巴巴地問一聲,有月票嗎?
本書由樂文首發,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