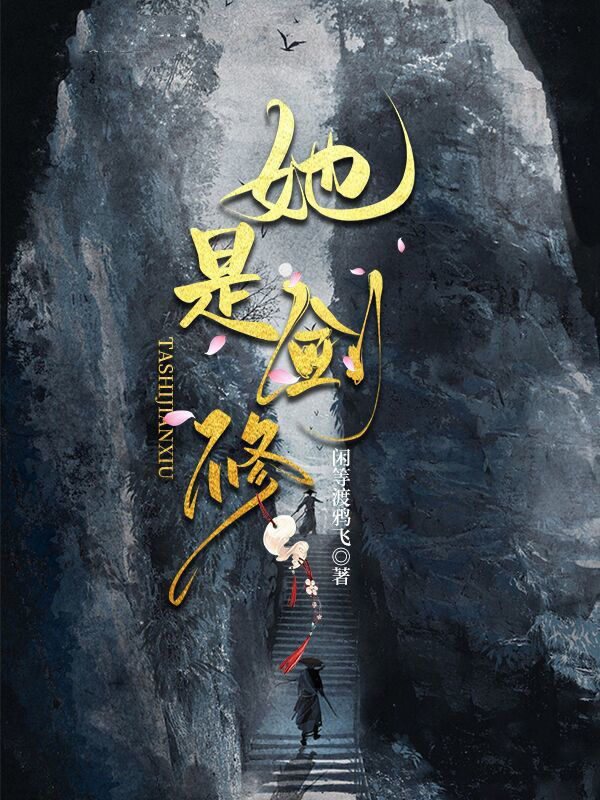這一戰一直持續了大半夜,一個個火把燒紅了西冷城上方的天空,喊殺聲震天!
來襲的西夜大軍完全沒有料到南疆軍竟然會殺了回馬槍,然而此時,就算西夜人明白他們中了大裕的誘敵深入之計,一切也已經遲了。
對于西夜大軍而言,此刻可謂是“前有狼,後有虎”。
黎明前,戰争終于平息,姚良航和韓淮君大步流星地踩在屍橫遍地、血流成河的戰場上,仍舊精神奕奕,明明一夜不曾歇息,卻沒有一點疲憊。二人并沒有整兵休息,而是率領玄甲軍和西疆軍趁勝追擊,一舉拿下了褚良城。
原鎮守褚良城的西夜大将則率領殘兵退守到三十裡外的荊蘭城。
這場勝利讓之前因為議和而受挫的士氣再次大振。
全軍上下都是一片歡騰,無不歡欣鼓舞,高漲的士氣直沖雲霄,唯獨韓淩賦黑着一張臉,面黑如鍋底。
這個時候,韓淩賦也弄明白了,姚良航和韓淮君其實算計利用了自己,偏偏自己以為這姚良航隻是個粗莽的武夫,低估了對方,所以才落入了對方的陷阱。
更可恨的是韓淮君,他身為韓氏子弟,身上還肩負皇命,竟然和南疆軍的人勾結在一起,枉費了父皇對他的信任,真真是可惡!
這筆賬他記下了!
與韓淩賦的憤懑相反,此刻姚良航和韓淮君卻是心情暢快,意氣風發。
當兩個青年從褚良城回到西冷城時,受到了城中百姓的夾道歡迎,在收複西冷城後,這個城池第二次迎來了生機。
兩人放緩馬速,讓馬兒不疾不徐地踱着步子,不時與路過的百姓、将士颔首緻意。
看着這些臉上又煥發出神采的百姓們,韓淮君的嘴角染上些許笑意,贊道:“姚兄,你實在是神機妙算!”
這一計誘敵深入使得妙!
這一仗赢得更是淋漓暢快!
“韓兄,這功勞我可不敢當!”姚良航笑道,言行之間看着與韓淮君熟稔了不少。
從最初的聯合作戰,到大前日殲滅辎重營再到今日這一戰的大獲全勝,兩個青年合作愉快,短短數日,兩人的情誼就邁進了好幾步。
當初在南疆時,兩人也就是一起喝過酒的交情,現在卻是知交好友了。
姚良航坦誠地繼續道:“我從南疆臨行前,安逸侯給了我幾個錦囊妙計。”他說得輕描淡寫,心裡暗暗歎息:何止是幾個錦囊妙計!安逸侯簡直就是算無遺漏!
韓淮君怔了怔,随即恍然大悟。
官語白,原來是官語白。
知西夜者,莫過于官語白!
想起那個荏弱的儒雅青年,無論是韓淮君,還是姚良航,都有幾分唏噓,也許這就是天妒英才……
靜默了片刻後,姚良航忽然話鋒一轉,正色道:“韓兄,這次恭郡王可能會上折子,你可有了打算?”
“……”韓淮君面色一凝,笑意僵在了嘴角。
姚良航緊盯着韓淮君的眼眸,緩緩地問道:“韓兄,你可敢抗旨?”
抗旨,抗的自然是與西夜議和的那道旨。
抗旨不遵,是殺頭滅族的大罪,韓淮君姓韓,就算不至于滅族,就算僥幸留下一條命,也是前途盡毀……
韓淮君的神色更為凝重,薄唇抿成了一條直線,隻是轉瞬,腦海中已經閃過了許許多多的畫面,想起他來到西疆後的所見所聞
疆土千瘡百孔
百姓四散流離
将士抛頭灑血、戰死沙場……
畫面最後停頓在那殘酷的戰場上,那一眼望不到邊際的屍體與鮮血,那一雙雙雙死不瞑目的雙眼……
不知不覺中,兩人都停下了馬,韓淮君垂眸靜思,而姚良航靜候在一旁,沒有催促,沒有出聲,此時,四周的喧嚣仿佛被一個無形的屏障隔絕了出去……
許久之後,韓淮君擡眼對上姚良航清澈的眼眸,一雙烏黑明澈的眼眸中綻放出堅定的光芒,緩緩道:“有何不敢!”
此時此刻,兩個年輕人的眼神是如此相似,淩厲,血性,皆是鬥志激昂。
姚良航朗聲笑了,豪爽地拍了拍韓淮君的肩膀。
這一次,他不是因為世子爺,而是他自己就相信韓淮君是條血性漢子,他知道韓淮君會做出正确的抉擇!
為了大裕,為了百姓,為了大義!
有些事,他們不得不為!
兩人繼續策馬前行,遠遠地,就看到守備府門口已經被玄甲軍的人團團包圍了起來。
見二人歸來,一個年輕的百将上前向姚良航抱拳禀道:“将軍,恭郡王的折子已經截下來了……厲大将軍和王副将他們現在也在府裡。”他雙手奉上了韓淩賦的折子,姚良航看也沒看,就遞給了韓淮君。
韓淮君随意地掃視了折子一眼,眸光閃爍地将折子收了起來。
他本來還在遲疑要如何處理厲大将軍他們,現在也不用再猶豫了……
這一日,一場大戰方歇,在所有人還沒反應過來時,西冷城中猛然又掀起了一波滔天巨浪,城中風聲鶴唳,大街小巷中遍布着一隊隊身穿铠甲、面目森冷的大裕士兵。
韓淩賦、厲大将軍、黃副将等一幹主議和将士鈞被軟禁在西冷城的守備府中,剛剛得勝歸來的韓淮君軍威正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掌控了西疆軍的大權。
當晚,西疆軍聯合南疆軍對荊蘭城的西夜大軍發起了猛攻,荊蘭城守了一夜後,城門岌岌可危,差點城破,然而,次日黎明,附近的砂江城在危急關頭派來一萬西夜援軍,敵我雙方又變得勢均力敵,激戰了一日一夜後,雙方形成膠着,僵持不下……
此後,零星戰火不斷,大裕幾次攻城都無法破城,西夜亦無法擊退大裕軍隊,如此膠着了好幾日。
前方戰報快馬加鞭地傳到了西夜都城,西夜王雷霆大怒,再度派出五萬援兵火速前往上黨郡,決心一鼓作氣拿下西疆,挫大裕威風。
西夜王以及西夜朝臣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西疆的戰事上,卻不知道大裕有一句俗語:“不怕前院點燈,就怕後院起火”,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有一支三千人的隊伍僞裝成了數支商隊從如今的七裡郡,也就是曾經的七裡國,進入西夜南境的迦南關。
迦南關乃是西夜最南方的第一座關隘,也是一幹西南小國進入西夜的必經之城,從迦南關一路北上,途徑翼落州、谷裡州就是西夜都城金九城。
迦南關可說是西夜的一道重要屏障。
當晚,當迦南關的西夜人還在安眠之中時,潛入關内的這三千人訓練有素地結集起來,風馳電掣地兵分兩路,對北城門和南城門分别發動奇襲……
守城的西夜将領急忙往兩邊城門調兵遣将,卻發現對手如同天降神兵,一個個皆有以一敵十之能,下手毫不留情,頗有幾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的氣勢。
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喊殺聲和兵器交接聲中,迦南關的南城門被幾人合力推開,那隆隆的聲音在黑夜中如同地龍翻身般,也仿佛是黑夜中響起的一個信号。
然而,此時的西夜人還不知道,西夜馬上就要翻天了!
南城門外,一支支火把點亮,數千名将士不知何時出現在那裡,為首的是一個身穿月白衣袍的青年,削瘦儒雅,淡定從容。
“滋吧滋吧……”
無數火把在空氣中熊熊燃燒着,昏黃的火光在青年的臉上灑下一層瑩光,他看來俊美非凡,風度翩翩,沉穩内斂之中英氣逼人。
在四周殺氣騰騰的氛圍中,這個如書生般的青年看來那麼突兀,就像是把文戲中的小生擺到了武戲中一般,有一種詭異的不和諧感。
“走!”
儒雅青年簡單的一個字落下後,便信步走在最前方,他身旁的黑衣青年悠哉地與之并行,身後的士兵們緊随其後,步履隆隆。
他們一進南城門,就有一個身披古銅色盔甲的娃娃臉青年迎了上來,正是傅雲鶴。
他抱拳對着官語白行了軍禮:“侯爺!”
“傅将軍,城中情況如何?”官語白淡淡問道。
兩人一邊往前走,一邊說着話。
“侯爺放心,”傅雲鶴挺直胸膛,一手握着劍鞘,看起來英姿勃發,“迦南關的南城門和北城門皆在我軍掌控之下,絕無任何一人逃出城外。現我軍折損七十人,殲滅敵軍五百人,俘虜三百人,敵軍還有三百人負隅頑抗……一個時辰内必可全數拿下!城中西夜百姓皆閉戶不出,暫時無傷亡……”
他的語調铿锵有力,眉眼之間更是意氣風發,曾經困擾他的心結在上次和蕭奕一番談話後,徹底解開了。
大哥既然能信任自己,毫不介意自己的身份,讓自己來領軍打這麼重要的一仗,他又何必鑽牛角,耿耿于懷。
正像大哥說的,他如今在南疆軍,身為軍人,服從軍命就是,别的也不用多想,他現在要做的就是助安逸侯拿下西夜!
想着,傅雲鶴的神色之中又有一抹複雜,飛快地瞥了眼身旁官語白俊朗的側顔。
他早就知道官語白和大哥蕭奕感情不錯……如今看來,恐怕比他所想的更好!
這兩人到底是如何成為知交好友的呢?!
他隻糾結了一瞬,就摸着鼻子不再多想,别人的事,何必管那麼多呢!
他現在該想的是,等這一仗打完後,他也能成親了。
霞表妹還在駱越城等着自己凱旋而歸呢!
傅雲鶴嘴角一勾,露出傻兮兮的笑容,隻聽官語白沉吟着又道:“傅将軍,傳令黎副将、遊參将、吳參将到守備府商議軍情!”
“是,侯爺。”
傅雲鶴立刻傳令下去,一炷香後,幾位将領便聚集在守備府的正廳内,一張偌大的書案被擺放在廳堂中央,書案上平鋪着一張巨大的輿圖,那輿圖上不僅是詳細标記了西夜的地形,還标了許多不同顔色的小旗子……
“西夜十二族,這十二種顔色旗子分别代表這十二族的分布……”
官語白垂眸盯着輿圖,修長的手指在輿圖上指點着,對着衆人徐徐道來。
占領迦南關僅僅是他們的第一步,這場戰役才剛剛開始,接下來才是真正的挑戰,這注定是一條由鮮血與生命鋪就而成的路,所以決不能出一點差錯!
廳堂内的氣氛分外凝重,也唯有一旁的黑衣青年無論神态還是肢體都尤為輕松。
他獨自坐在旁邊的一把高背大椅上,悠哉地給自己斟酒,還招呼一旁的小四也過來喝酒,可是小四根本就充耳不聞,目光一眨不眨地看着衆人中心的官語白。
司凜也順着小四的目光看去,官語白的表情是那麼全神貫注,一雙烏眸中平日裡的溫潤不在,取而代之的是銳氣,是殺氣。
這是他所知的官語白,曾經的官語白,本來的官語白!
官語白本來就是皇帝用區區一個“安逸侯”的名号就可以豢養的。
他并非溫順的綿羊,而是一把絕世名刀,這把刀本該屬于皇帝,現在卻“陰差陽錯”地落入蕭奕手中,對大裕而言,這究竟是福,還是禍呢?!
司凜仰首将杯中之物一飲而盡,勾出一抹似笑非笑,這又與他何幹?
反正語白高興就好!
夜色緩緩地過去,當一幹将領從守備府時走出,外面的天色已經是蒙蒙亮了。
衆将各歸各營,休息整頓,然後于次日起繼續喬裝北上……
西夜那邊的戰線正如官語白和蕭奕計劃般步步推進,蠶食鲸吞而駱越城裡,于修凡、常懷熙和閻習峻等一衆新銳營的小将卻很是郁悶,這些日子以來,他們每日在駱越城大營當值時都絞盡腦汁地在蕭奕面前晃悠,試圖委婉地提醒蕭奕,卻是未果,新銳營直至今日都沒有得到任務。
九月十七,于修凡、常懷熙和閻習峻正好休沐,三人就約了在踏雲酒樓喝酒,也順便商量一下對策。
三人進了二樓慣常坐的雅座之中,于修凡一口氣就叫了三壇酒,口口聲聲說要無醉不歸。
當酒壇打開後,雅座中酒香四溢。
于修凡的口涎開始分泌,酸溜溜地說道:“小鶴子現在可沒這好酒喝,我們三人幹脆連他的份一起喝了!”傅雲鶴領兵在外,自然是不能喝酒的。
常懷熙和閻習峻無語地看着于修凡,人又不在這裡,他耍這種嘴皮子有意思嗎?
于修凡讪讪地摸了摸鼻子,給兩個兄弟倒了酒,然後道:“小熙子,小峻子,你們說世子爺這次不會真的不打算用我們新銳營吧?”
姚良航走了,傅雲鶴走了,連官語白都走了!
于修凡三人雖然不知道世子爺在計劃着什麼,但已經隐約感覺到也許這一次世子爺所圖不小。
如今,也就他們新銳營的人還被留在南疆,于修凡心裡還真是有種被撇下的失落感,幸好還有小熙子和小峻子“陪”着他……
常懷熙執起一個白瓷酒杯,一飲而盡,道:“那倒也未必。你别忘了,世子爺還在城裡呢……”
也是!于修凡心念一動,面露喜色,起身正欲再給常懷熙斟酒,卻見對方的視線正看向外面的街道,便也循着他的視線看去……
酒樓外的街上人來人往,不少路人都齊刷刷地看向了同一個方向。
不遠處的百花樓外,一個六七歲面色蠟黃、身形瘦小的女童正歇斯底裡地哭喊着:“不要……不要。大伯父,囡囡要回家,囡囡要回家找弟弟……哇!”
女童一邊嚎啕大哭,一邊試圖往另一個方向逃去,可是一個胡子邋遢的中年男子死死地拉住了她的手,嘴裡咒罵着:“臭丫頭,你不去也得去!老子我都收了人家的銀子了。”
這一大一小吸引了不少路人駐足,有一個中年婦人對着他們指指點點道:“也不知道這小丫頭的爹娘在哪,這做人伯父的竟要把親侄女賣到百花樓那種腌臜地方去!”
“就是就是!也不怕以後生了兒子沒屁眼!”她身旁的老婦憤憤地附和道。
就在這時,她們身後傳來一個清冷的女音好奇地問道:“這位大姐,我看這百花樓布置得雖有些華而不實,但看着也算一家不錯的酒樓,為何大姐你要說它腌臜呢?”
兩個婦人都是循聲看去,隻見一個十四五歲、身穿青色棉布衣裙的少女就站起她們身旁,瓜子臉,面容清麗,一臉疑惑地看着她們倆。少女身後還跟了兩個丫鬟模樣的小姑娘。
也是,小姑娘家家的,恐怕是不知道百花樓是什麼地方!兩個婦人面露一陣古怪之色,随即,那中年婦人就解釋道:“姑娘,你是不知道,這百花樓是煙花之地,又怎麼會幹淨!”
煙花之地……青衣少女自然是知道的,眉頭微蹙,朝那中年男子和女童看去。此人身為長輩,卻是為老不尊,真真是可恨!
對于踏雲酒樓的于俢凡等人而言,這個青衣少女委實看着眼熟……
于修凡脫口而出道:“咦?這不是大哥的妹妹嗎?”
話落的同時,臨窗而坐正在飲酒的閻習峻也是急忙往外望去,三個青年的目光都看向了一身素衣打扮的清麗少女。
不錯,那個青衣少女正是喬裝出行的蕭霏。
蕭霏轉頭吩咐了桃夭一句,桃夭就大步上前走到那邋遢的中年男子跟前,脆生生地說道:“喂!這小妹妹你要賣多少銀子?”
那中年男子有些意外,看了看丫鬟打扮的桃夭,又看了看她身後的蕭霏,覺得蕭霏最多不過是個米鋪、酒鋪的小戶千金,就算家裡養的起兩個丫鬟,能有銀子再多養一個嗎?
而且,這百花樓可是出了十兩銀子啊!
中年男子咽了咽口水,獅子開大口道:“十五兩,不,二十兩!”
在男子貪婪的目光中,桃夭從錢袋裡掏出了兩個銀錠,正要丢給對方,就聽一個尖銳的女音自右前方傳來:“誰敢搶老娘的人?!”
随着話語聲響起,一個濃妝豔抹的老婦從百花樓中走出,身後還跟着兩個彪形大漢,一看就不是善類。
那老婦,不,或者說老鸨,扭着腰身走了過來,叉腰高氣昂地對桃夭說道:“小姑娘,為人做事要講先來後到,這小丫頭片子,老娘我已經給了銀子了,就是我百花樓的人。就算是皇帝老兒來了,也别想帶走這小丫頭!”
中年男子盯着桃夭手裡的銀子,心裡一陣惋惜,可惜老鸨說得不錯……而這百花樓,他也得罪不起!
聽着老鸨粗鄙的言辭,蕭霏微微蹙眉,上前走到桃夭身側,淡淡道:“我願出二十兩銀子,你可否将這小妹妹賣與我?”
二十兩銀子雖然不錯,但是對于老鸨而言,這吃進嘴巴的肉就沒有吐出來的道理,更何況,她還指望着養大這小丫頭以後給她掙幾百兩幾千兩呢!
“不行。”老鸨堅決地說道,輕蔑地審視了蕭霏一番,“丫頭,瞧你細皮嫩肉的,老娘勸你别多管閑事,免得傷了你如花似月的臉蛋!”
說着,老鸨揚起手,對着身後的兩個彪形大漢揮手使了個手勢,然後指向那個女童不悅地拔高嗓門,“還不給老娘把這小丫頭給帶走了!”
“如果我一定要管呢?”蕭霏看着老鸨又道,語氣雲淡風輕。
老鸨眉頭一皺,用胖乎乎的手指指着蕭霏道:“給老娘教訓……”
“汪!”
一聲興奮的狗吠聲打斷了老鸨,一道灰影飛似的閃過,朝老鸨撲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