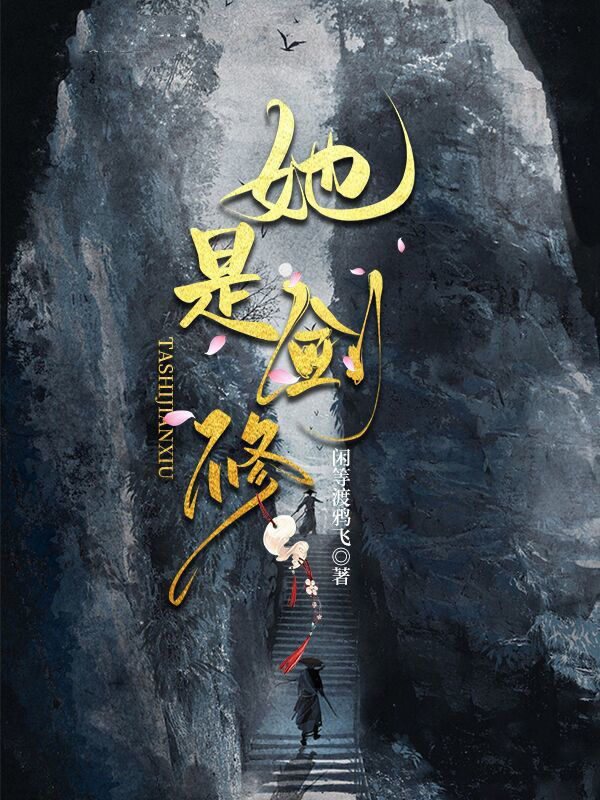如今的大順朝,已非往昔,皇上不僅把燕王下了大牢,更将太後、皇後以及太子趕出了皇宮,要說燕王是因為維護梅記被責罰,可生養扶持他的太後,端莊賢良的皇後,勤學恭謹的太子又何錯之有?
我爹和朝臣們多次上折,勸告皇上不要偏寵春貴人這個妖女,可皇上根本不聽,反而變本加厲将她晉升為春嫔,更多次在朝會上斥責直言規谏的臣子。
眼下,蜀王憑借這個不知哪裡來的幹妹妹,在皇上跟前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而他韬光養晦十多年的圖謀,明眼人都看得出,唯有皇上一葉障目,不辨忠奸!
今日之情形和十多年的内亂前夕何其相像,老将軍,這江山是您們打下來的,當年四海稱頌的結拜兄弟,如今也隻剩您一人,難道您要眼睜睜看着它被颠覆,百姓再次飽受戰亂之苦嗎?”此時的宋少淮神色鄭重,說話擲地有聲,竟找不出半點纨绔模樣。
“老将軍總有些舊部親信可以聯絡,此時尚可力挽狂瀾,不緻重蹈十多年前的覆轍。更何況,當年之事更像一場陰謀,老将軍不想查明真相嗎?”慕容熙端起酒杯在鐵戰杯下一碰,率先一口喝盡。
聞言,鐵戰身軀一震,朝堂上的紛争,他可以不管,可他們兄弟浴血打下的江山,斷不能葬送在昏庸無能的人手上,更何況慕容熙戳中了他的傷心事,他的兒子鐵冀就是在十多年前内亂中戰死的,這會兒,被慕容熙冒然提起,心中不免酸楚。
“我那些舊相識都散在各處,大多在燕地定北軍中,如今,定北軍的主帥是甯皇後的父親甯征,而她的哥哥甯鵬遠鎮守邊塞燕城,若皇後被驅逐的消息傳過去,必然引起騷動,到時蒙古察部趁亂滋擾,邊關又将不得安甯。”鐵戰滿飲一杯,不無擔憂道。
“皇後娘娘賢良淑德,最能顧全大局,這會子明面上還是出宮祈福,她就是打落門牙和血吞,也不會将這事傳遞給邊塞父兄讓他們為難的,怕隻怕有人冒用她的名頭,故意傳遞假消息,誘甯家父子率兵入京,到那時,事情一旦敗露,甯家必将身敗名裂,滿門抄斬。”宋少淮以手指敲擊桌面,他擔心的是另一個陰謀。
“這個,暫且不用擔心,密宗情報網現已全部啟用,所有從江陵城傳遞出去的消息,都被我們的人攔截謄抄下來,尤其是送往各大軍營的。今早,我們就攔截了一封從蜀王府送給駐紮在城外十裡虎威軍的信。”慕容熙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封火漆緘口的信。
幾人傳遞着看了看,信封上隻寫着任兄親啟的字樣,觀之并無異常,仿佛隻是一封再尋常不過的家書。
“鐵夫人,麻煩您給我一碗清水。”慕容熙轉頭說道。
朱氏很快端來了一碗水,慕容熙将棉帕子浸濕,覆在沒有火漆封口的另一端,稍等片刻後,慕容又向朱氏借了一根針,慢慢将信尾挑開,從裡面拿出一張紙。
幾人圍攏了一看,這封信是寫給虎威軍督軍任富成的,其上并未提及軍事,隻寫了新置辦的田産房屋等等。
“這……”宋少淮不明就裡,難道這真是封家書嗎?
“看不出來?這分明是份禮單,千畝良田,五處豪宅,不要說他一個督軍,就是你父親,中書令大人,這麼多年的俸祿銀子能在江陵城中買下這些嗎?”慕容熙抖了下紙,笑着說。
“世人都說我是纨绔,看來江陵城中,比我家有錢的,多得是呢。”宋少淮連連搖頭。
“蜀王肯定知道密宗會收集情報,這很可能是個假消息,就算是真的,單憑這張紙,也不能證明任福成與七王勾結謀逆。”鐵戰是沙場老将,兵法三十六計谙熟于胸。
“我會将這封信原樣送過去,到時看他如何反應,是敵是友,一目了然。”慕容熙照原樣将紙重新折好,放回信封裡,又将封口粘上了。
“離江陵城最近的就是虎威軍,楚霑無論是逼宮,還是切斷其他地方的勤王援軍,虎威軍都是重要的關隘,他自然是要拼命拉攏。
而他為什麼要和督軍套近乎,而不是直接找軍中主帥裴慶,想來他也知道裴慶是徐侯爺最得力的部将,你們不如尋他,倒比我這過氣的老頭兒管用的多。”鐵戰又倒了一杯,仰脖将烈酒一口咽下。
“若是我們得了這十萬虎威軍的助力,兵谏何愁不成!”宋少淮暗暗盤算了一下。
“阿梅病中,我們縱使拿了紫檀簪去,隻怕裴将軍也不會聽我們的,還要将我們當竊賊抓起來。”慕容熙眉峰微擰,為難道。
“那丫頭的傷,還沒有起色嗎?”鐵戰捋了下短而粗的白須道。
“箭傷倒是大好了,隻是她昏迷日久,時好時壞,有時能聽懂人言,有時又好似不能,鐘大夫說她的魂靈沉在幻海裡,不知何年何月才會醒。”慕容熙咬了下嘴角,痛苦道。
“有道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她是個勇于承擔的姑娘,或許需要一個非常大的刺激,才能将她的魂靈拉回來,她當初是為燕王擋箭,如今,燕王又陷困局,還有梅記和她妹妹牽連其中,你們不如背水一戰,試上一試,若是她能醒來,很多事将會迎刃而解,若是不能,不過還是昏迷,并沒有更多壞處。”鐵戰拿起酒壺,給每個後生晚輩倒了一杯。
“這……”宋少淮看了眼慕容熙,後者也在看他。
“你們隻知紫檀簪和血藤簪可以号令三軍,卻不知同時握有紫檀簪和血藤簪的人,不僅可以号令三軍,還能斬殺違令者,更能上懲昏君,下誅逆臣。
當年徐侯爺身故之後,并沒有發現紫檀簪,這讓我們一直堅信萩白還活着,但因紫藤簪暗含的權利十分巨大,也引得惡人一直在追殺。如今杜梅的身世大白天下,又被敕封為清河郡主,她弟弟尚小,這會兒,她便就是忠義侯府名正言順的繼承人。
我已老矣,心有餘而力不足,隻等着你們帶梅丫頭來拿血藤簪,轟轟烈烈去幹一番大事!”鐵戰鄭重地和宋少淮、慕容熙碰杯,而後一飲而盡。
面對這樣艱巨的托付,宋少淮和慕容熙站了起來,什麼話也沒說,隻将杯中酒悉數喝下,這是無聲的承諾。
雪靜靜地下,四匹馬同行,馬蹄踩在綿軟的雪地上,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街市上空無一人,連兩邊的店鋪都早早關了門,大紅燈籠上落了雪,被風一吹,又撲簌簌地直掉。
袁瑾年因父親的所作所為,令他在兄弟面前十分難堪,故而他不想回家,隻在燕王府中将就了一晚。
慕容熙要回去處理那封信,宋少淮不放心他爹,故而他兩人各自回去了,分别時約好,明日一起到杜家溝去。
楚霖自打那日吃過早飯離開,便再沒有過,許氏屈指算算,早超過了他平日間隔的日子。那日,許氏在杜梅枕下發現了一根上好的碧玉發簪,簪頭上有一點黃沁,被巧雕成了幾朵小小的臘梅花,看那手藝并不像出自玉雕大家之手,卻勝在心思精巧。
許氏心裡不安,楚霖留下的發簪明顯和他自己戴的那根是一塊料子上的,他悄悄留下這個,一句話都不說,人也不來了,莫不是江陵城中出事了?
相較于許氏将這種擔心藏在心裡,杜梅的反應則明顯得多,在楚霖沒有按時來後,她時常蹙眉,身上更是冰冷地發抖,哪怕屋裡燃着火盆,對她也是于事無補。
許氏每日堅持給她紮針按摩,有時候能聽見她嘤嘤的聲音,或者被她無意識地抓住手,但也僅限于此,再沒有旁的變化。
這一日,鵝毛大雪下了一天一夜,許氏睡得不安穩,一會兒琢磨楚霖為什麼不來,一會兒又披衣起來,看看杜梅房中的炭火,直到後半夜才囫囵迷糊着了。
天還沒有亮,窗外晶瑩的雪映照到屋裡,有朦胧的亮光,杜桂散着頭發,猛地跑進了許氏的屋子:“娘,我怕!”
“怎麼了,桂子不怕哈,是不是做噩夢了?”許氏趕忙将杜桂攬到被窩裡。
“我剛才夢見二姐和小七姐被關在一個黑屋子裡,還有苗嬸子抱着個娃娃,那娃娃一直哭,一直哭,可慘了。”杜桂想起夢裡的畫面,忍不住吸鼻子。
“什麼!”許氏大驚。
許氏驚的不僅僅是杜桂突然有了預見未來的能力,還在于她第一次預見的,竟然和杜櫻有關,還牽扯到一個娃娃,這娃娃又是哪裡來的?
她不知道杜桂預見的事,是即将發生,還是在幾個月之後,亦或是更久遠,她垂頭看了眼窩在她懷裡的女兒,顯然是被這個夢吓着了,蜷成一團。她終究忍了忍,沒再問,可她心裡的不安,卻因杜桂的這個夢更加清晰起來。
她待杜桂睡着了,便披衣起床,杜梅屋裡還是昨日的樣子,并沒有人來過,許氏坐在杜梅床邊,給她掖掖被角,低聲呢喃:“梅子,你快些醒來吧,櫻子獨自在江陵城,我心裡總怕出事。”
一如既往地沒有任何回應,許氏歎了口氣,給炭盆又加了些炭,轉身去廚房,當她關門的時候,并沒有看見杜梅的睫毛在劇烈地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