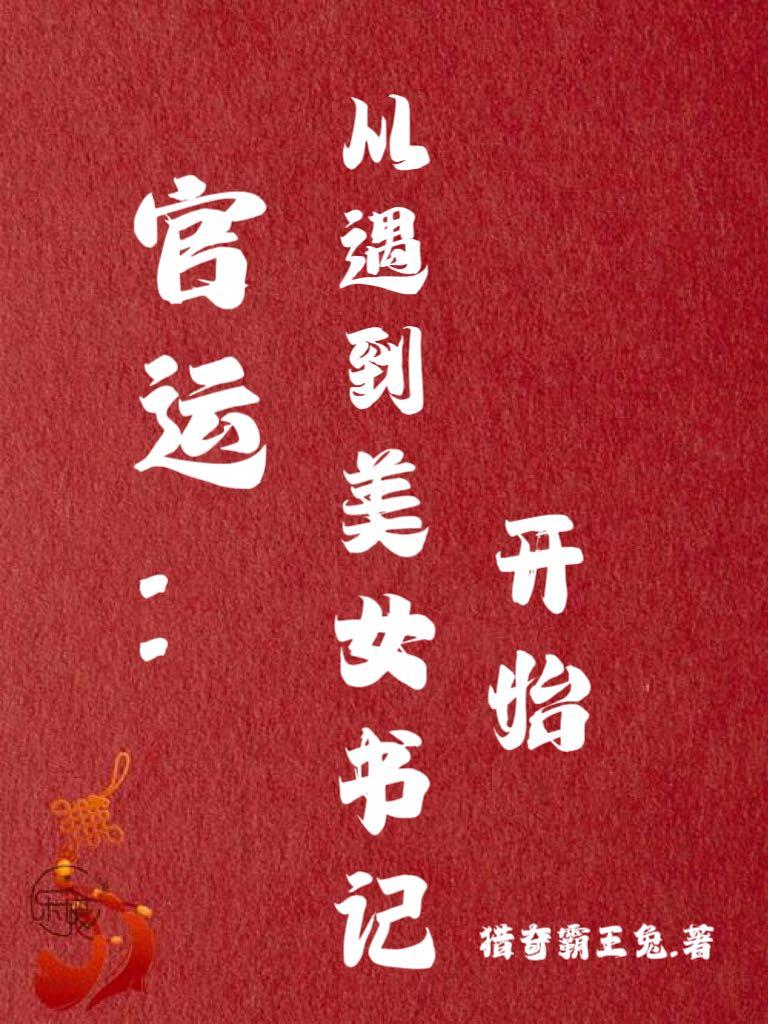不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以林念念和景灏的狠辣程度,讓他們知道他們做這種事,被唐蘇看到,他們不可能讓她活着離開包間!
“唐蘇,我沒有多少耐心,我給你三秒鐘考慮的時間!若你繼續執迷不悟,你這輩子,都别想翻身!”
景墨心裡清楚,他用這種條件威脅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真挺卑鄙的,他雖然從來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但也不屑用這種不入流的手段威脅一個女人。
但是怎麼辦呢,他太想要唐蘇了。
想得心都疼了。
她就像是一個魔咒,萦繞在他的腦海心中,午夜夢回,他每一次在睡夢中揮汗如雨,都是為她。
景墨對自己強大的自制力向來滿意,這種一次次近乎癫狂的失控,讓他心中不爽又憤怒。
他深信自己不可能愛上唐蘇,所以,他對她,隻是男人對女人身體的追逐。
或許,得到了她的身體,他就不會再為她癫狂成魔,他也不會,變得越來越不像自己。
“景先生,你别碰我!”
唐蘇不想驚動外面的林念念和景灏,但她也不想讓景墨得逞。
她用力踩了他一腳,趁他怔愣的空檔,她快速從他的鉗制中鑽了出來。
浴室裡面的空間,真的是太小了,對于他的步步緊逼,她根本就無處可逃。
她想要沖出去離得他遠遠的,但外面有林念念和景灏,她出去,處境隻會更危險。
“唐蘇,你果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絲毫不給唐蘇任何逃離的機會,景墨手上用力,直接将她按在了地上。
“景先生,你放開我!若是讓景灏發現你在這裡,你也别想全身而退!”唐蘇深吸一口氣,努力讓自己保持鎮定。
“是麼?”
景墨絲毫沒有将唐蘇的威脅放在眼裡,“唐蘇,你覺得我會怕他?!”
的确,現在的景墨,已經完全不必将景灏放在眼中。
景墨回到景家之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景家所有的勢力、财富,都已經交到了他手上,而景灏,不過是挂着景家二少頭銜的一具空殼子,他動動小指頭,就能捏死景灏。
“唐蘇,你不過是個肮髒的女人,論斤賣肉,陸淮左他們都能買你,我景墨也可以!”
景墨眸中的火焰燃燒得越來越可怕,唐蘇想要狠狠地甩他一巴掌,把他打醒,可她又怕,制造出的聲音太大,會驚動景灏和林念念,隻能咬着牙收回了手。
景墨也是看出了這一點,他身上的動作,越來越放肆,“唐蘇,别總是一副被人欺負的貞潔烈女模樣!若不是你這張臉尚且能看,就算你主動投懷送抱,我景墨都不要!”
“一千萬,陪我一次!今晚之後,我們銀貨兩訖,再不相幹!”
一千萬一次……
呵!
唐蘇低低地嗤笑,景墨可還真瞧得起她啊!
可惜呢,這賣肉得來的錢,她唐蘇嫌髒!
用力吸了一口氣,唐蘇已經竭力保持冷靜,但她的聲音中,還是帶了明顯的顫栗。
“景先生,我說過,我唐蘇看上的男人,不用給我錢,我願毫無保留地把自己交給他,與他同生共死,不離不棄!可我唐蘇瞧不上的男人,不管給我多少錢,我都不屑!”
“景先生,一次次強迫一個根本就瞧不上你的女人,真沒意思!”
“唐蘇!”因為太過憤怒,景墨的聲音不由得拔高了幾度,不過幸好門已經關上,再加上林念念和景灏太過投入,他們根本就注意聽到浴室裡面的聲音。
“唐蘇,你再給我說一遍?!”
“景先生,我瞧不上你,所以,請你别再自取其辱了!”
景墨氣得玉白的一張臉徹底黑成了濃墨。
瞧不上他!
又是瞧不上他!
他景墨,到底是哪裡比不上陸淮左還有林翊臣他們!
在别的男人面前,她什麼下賤的讨好都願意做,在他面前,卻裝良家女上瘾了!
真特麼惡心!
惡從心生,景墨說出來的話,愈加的陰冷刻薄,“唐蘇,你以為我就瞧得上你?!我要上你,不過就是想要嘗嘗,海城最下賤的這隻雞,到底是什麼滋味!”
“唐蘇,我隻願,我們銀貨兩訖之後,你别不要臉地纏着我不放!”
見景墨又開始發狂,唐蘇急得額上都滲出了細密的汗珠。
林念念和景灏,絲毫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她出,出不去,在這裡,似乎隻能任景墨宰割!
可她不願意成為景墨的女人!
哪怕,在地牢中,他們相依為命的時候,她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她要成為他的女人。
“景墨,如果你想再逼我死一次,你大可以繼續!”
景墨的身子,陡然一僵。
他死死地盯着唐蘇,那雙越來越冷峻的眸中,一瞬間被無邊的猩紅充斥。
他咬了咬牙,他想說,唐蘇,有種你就去死!你這種髒女人,死一萬次也是活該!
他發現,這種話,他說不出口。
因為,他怕極了她會死。
而她,也真的會死。
那次他對她用強,她割腕自殺,那一大片刺目的鮮紅,他這輩子,都不會忘卻。
景墨攥緊了拳頭,狠狠揮下。
唐蘇以為他是要揍她,她下意識地閉緊了雙眸。
意外的是,景墨這拳頭,沒有揮到她身上,而是砸在了一旁的地面上。
“唐蘇!”
他猛地擡起臉,一瞬不瞬地望着她,如同跌落深淵、求生無門的猛獸。
他的聲音,驟而低了好幾分,“唐蘇,為什麼?”
唐蘇怎麼都沒有想到景墨會忽然問出這麼一句,她有些懵。
沒頭沒尾的一句話,鬼才知道為什麼!
“唐蘇,為什麼你能喜歡别人,卻總是瞧不上我!”
“為什麼?!”說道最後,景墨的聲音,都有些嘶啞,如同被人扼住了喉嚨,絕望嘶吼。
唐蘇沒有立馬說話,而是眼睑低垂,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的左手。
她左手上的繃帶,又被血液滲透了,也該換了。
她不疾不徐地解開左手上纏得厚厚的繃帶,拆最裡面一層的時候,因為被膿血黏在了一起,很疼,她忍不住輕輕蹙了下眉。
她揚了揚自己的手背,帶着幾分厭世的自嘲,“景先生,我沒有受虐傾向。如果我一次次不分青紅皂白,折磨得你遍體鱗傷,還剁掉你一根手指,你可會喜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