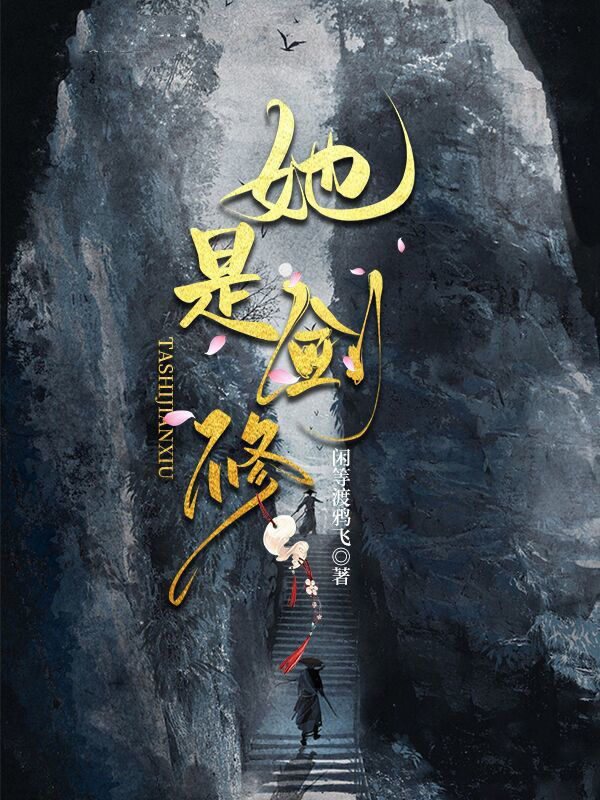叢州,金河灣。
綿長的號角聲飄蕩在河流兩岸,屈牙族妖修齊聚於河畔,為首的女性族人懷抱一隻幼狼,俯身從緹金之河中以手舀起河水,在幼狼背脊上澆濕撫過。
這是數十年來降生在金河灣的第三隻屈牙族幼獸,正在母親的懷抱中受著聖河之水的洗禮。
愈是血統高貴的妖族精怪,族中就愈是繁衍艱難,屈牙族作為古妖奔流巨狼的後裔,自也受此困擾已久,是以每一位新生兒的誕生,於他等而言都是生命的禮讚,值得盛大的慶典與徹夜狂歡。
“族巫定下了她的名字,喚作納伊,在妖族古語中寓意著安寧。”柳萱含笑望著屈牙族妖修們舉臂歡呼,她與趙蓴並肩而立,神情坦然而溫柔。
妖族精怪的聚落裡,往往存在著一位巫。而在古老的傳統中,族巫意味著先知與預言。雖然血統衍變至今,導緻族巫再無先知預言之能,但對聚落十分重要的製藥與製器等手段,還是使巫擁有了僅次於妖尊的地位。
為新生兒命名,便是族巫的權能。
“隻可惜,眼下並不夠安寧。”趙蓴的目光從幼狼移到其母身上,這位屈牙族妖修的眼中,尚帶著對孩子的寵溺,與幾分眷戀、哀愁。
她與柳萱已在金河灣中度過十載歲月,這十年落於修士眼中,本是彈指一揮間,奈何正值魔劫爆發之際,才使諸多生靈不敢安枕而眠,亦不得安寧度日。
近年來,禁州邪魔異動連連,更兵分兩路,一路直指洞明關,一路則向著叢州而來。
而約莫三四年前,人族一方又獲知蠻荒邪修俱倒戈向邪魔屍鬼之流,此舉深深壯大了敵軍勢力,亦叫三州內群情激奮,恨不得領兵踏平邪修諸宗,叫背叛之人曉得正道的利害手段。
不過蠻荒之內勢力複雜,眾人遂心中不忿,卻也始終不得要法便是了。
“阿蓴近來,可有什麽突破之感?”柳萱偏頭問她,笑意盈盈。
趙蓴卻是搖了搖頭,答道:“總是差了幾分火候,離歸合後期怕還要些積蘊才是。”
這十年裡,有柳萱煉製的無瑕神闕丹供養,卻也隻叫她丹田道台上的兩座神像虛影有凝實的跡象,而若想突破到歸合後期,還得繼續修行方可。由此也見,這兩座神像虛影,修行起來的難度確是比旁人高過不少。趙蓴隻得希望突破之後,實力也能隨之大漲。
柳萱輕歎一聲,倒也不覺如何焦急,隻寬慰道:“你畢竟與一般修士不同,多修行些時日也是好的,屈牙族庫中尚還存餘不少襲明草,不管如何,總是足夠的。”
先頭所贈的百株襲明草,未過多久便叫柳萱用完了。她心思轉動得快,將所煉神闕丹中的無暇品質交由趙蓴後,便取了剩下的靈丹予屈牙族妖修試作吞服。妖族精怪們隻是偏重於肉身體道修行,對元神並非全然不顧,見服食了這神闕丹,能使元神之力有壯大之相,即對柳萱的手段嘖嘖稱奇起來。
他們甚少與人族修士相交來往,亦極少體會靈丹之妙,如今見神闕丹效用神奇,亦是對人族修士消下了幾分偏見與懷疑。
而妖王們自也樂得見到族中妖修有所進境,對此也便當做不知。
此後柳萱便將無瑕品質的神闕丹留給趙蓴服用,其餘品相的丹藥則賣與屈牙一族,如此互利往來,也叫屈牙族拿出襲明草來的態度更加爽利暢快。
是以才叫柳萱有此一語。
兩人行至客居之處時,正巧見得羽叱與牧縈兄妹二人在門口等待。
“找你的?”柳萱努了努嘴,忍不住打趣道。
屈牙一族的妖修大多性情桀驁,直白些講就是兇猛好鬥。這些年裡趙蓴在金河灣中,便常被羽叱邀去比鬥,他一身實力比牧縈強過不知多少,雖不能與凝結了道種的歸合大圓滿修士相較,但在歸合後期中,實也能稱作佼佼者了。
放於人族三榜,至少也是淵榜前十的層次!
而屈牙族的少族長金邶,甚至還要強過於他,即可見這些古妖後裔,的確臥虎藏龍。
趙蓴初次與羽叱交手時,留在金河灣修行的日子尚還不足一年,修為上亦是無多進境,是以未過多久便落到下風,最後險險落敗。
不過在這種點到即止的比鬥中,她也未曾施展《太蒼奪靈大法》此類底牌一般的手段,倒還算有所保留。
至後來修行愈久,道台神像愈見凝實,和羽叱的比鬥也便贏多輸少,最後使之心服口服了。
眼下瞧見羽叱兄妹,即又叫柳萱想起此輩糾纏邀戰的情狀,一時失笑。
“我看不然。”趙蓴凝神一掃,霎時就了然於心,反是略有深意地回看向柳萱,抿了抿唇。
羽叱若是為邀鬥而來,身上必然有勃發戰意不容忽視,而此刻在兄妹二妖身上,卻是憂慮大過鋒芒,顯然是懷有心事。何況看向行來的兩人時,兄妹二妖都是隱隱將視線落在了柳萱身上,趙蓴若瞧不出今日他們來尋誰,那才叫怪事。
“趙真人,柳丹師!”
兩人來此十年,諸多屈牙族妖修亦是學會了人族常喚的稱謂,隻是因柳萱丹道手段奇絕,使得他們皆不願稱其作真人,反而一味稱之柳丹師。
“兩位道友,”趙蓴與柳萱起手見禮,又問,“正是在賀新生之慶,兩位怎的到這處來了?”
兄妹二妖都是直言不諱的脾性,便由兄長羽叱率先開口,說道:“實不相瞞,這回又有邪魔屍鬼欲從邊關破入叢州,好在被千須樹林阻下,才未叫它們成功得手。
“卻不知曉這些邪物放了什麽東西在林中,現下千須樹們皆都有陷入沉眠的征兆,我等叢州妖族不敢輕視,便約定了一齊過去探查古怪,此回便是由我兄妹兩個先行前去。
“又聽聞那處滋漫了不少毒瘴出來,這才想著來問問柳丹師,有沒有什麽解毒避障的靈丹可使的。”
一席話,說得趙蓴與柳萱面色都沉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