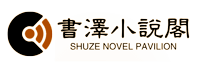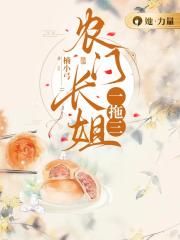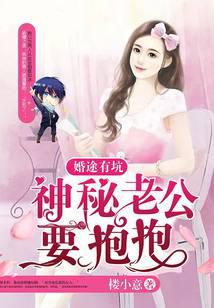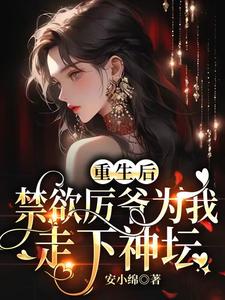說完潘氏在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又按上手印,兩份雇工文書,一式兩份,阿滿這邊一份,潘氏自己留一份。
阿滿送潘氏出去的時候,提醒了一句,“外婆可給您講了楊家的規矩?家裡沒分家,每房掙的錢都要上交公中三分之二。”
“知道,昨天娘就給我們說了,這規矩也沒錯,家裡的開銷都是公中支應,我們掙的錢自然該上交公中。
娘還給我們每房留三分之一,村裡打問完也就咱家這樣,娘很開明。”
幹了一中午活的馬氏,這才從錢氏嘴裡知道掙錢的事,氣的她當場撂挑子,被這個棒槌哄了。
中午楊家一家人吃飯,楊二舅把營生的事說了,一桌人心思各異,不過大抵都是高興的。
沒分家,每房掙的錢,家裡都能花,掙得多大家都能沾光。
“這騾子,二弟是從阿滿那借的?”馬氏盯着門口樹下的騾子說話都是酸溜溜的。
雖說阿滿也沒說不讓自己幹,可誰不知道她家男人和兒子老實的很,讓他們去賣東西,估計能賠死。
眼看有能掙錢的事,自家幹不成,反而讓二房占了先機,她心裡就不痛快,想找茬。
錢氏加一口蒜茄子搗嘴裡,啪一聲放下筷子,不滿的看大嫂:“我和二宏可不是什麼占便宜的人,不像有些人老想着從别人口袋裡摳錢。
這騾子是阿滿租的,一天十文錢呢。”
馬氏被噎了一下,不情不願閉上嘴,低頭扒飯,一桌子人心思各異,隻有馬氏對二房比他們先掙錢耿耿于懷。
說白了,她就是看不得二房比自家過得好,看不得錢氏嘚瑟。
潘氏趁機把她和三宏,要去阿滿和蘭靜鋪子做工的事說出來,氣氛又不一樣了,馬氏氣的都想摔碗了。
一個個眼刀甩給自家男人,這個窩囊,一家三兄弟,就他最沒本事。
“文山,你也去阿滿和蘭靜鋪子做工去,都是親戚,這阿滿總能答應吧!”
楊文山老老實實吃飯,沒想到被點名,一張黑臉漲紅,說話都結巴了,“娘,娘,俺...俺不行,不行的....”
看着手擺的像油炸一樣的兒子,馬氏心裡更氣悶了,自己這麼聰明的人,咋就生出這麼個不開竅的兒子,怪不得來村裡這麼久。
有人打問文海成親沒,就沒人打問文山成親沒,真真是個榆木疙瘩。
“好了,你還吃不吃,不吃就下桌。”江氏看大孫子漲紅的臉,有些氣惱,這個馬氏真是一點也不知足。
孩子啥性子早就定下來,就是硬逼着文山去學文海,那也是不行的,人壓根就不是吃這碗飯的,強逼着最後隻能雞飛蛋打。
馬氏低着頭不再說話,文海看看一旁失落的大哥,伸手拍拍人肩膀,堅定地說,“大哥,你一定會有你擅長做的,隻是現在還沒發現罷了,弟弟信你。”
文山默默點頭,臉上的失落散去幾分。
中午飯一吃飯,楊大舅心裡憋着火,扛起牆邊的鋤頭就往外走,頂着大太陽下地去了。
江氏眼裡看着,心裡也心疼,龍生九子還個個不一樣,雖然都是自己生的兒子,她也沒辦法讓孩子都厲害。
楊大舅心裡也氣悶,氣自己窩囊沒本事,氣婆娘不顧自己面子,不理解自己,心裡一天天就想着和二弟一家比。
鋤頭一下下重重砸在地裡,留下一個個坑。
第二天,楊二舅和兒子帶好衣服和幹糧,趕着騾車往離和關鎮最近的東豐鎮而去。
和關鎮附近除了東豐鎮,再離的近點的就是大營鎮、民安鎮、北通鎮。
錢氏不放心父子倆,送出老遠,“路上慢點,出門在外,手裡的
銀子不要不舍得花,窮家富路,給老娘一個個全須全尾回來啊。
算了,銀子能省還是省些!”
文海噗嗤笑了,“知道了,娘,别忘了我給你說的事!”
“臭小子,就惦記着那點兒事,這次給老娘好好賣,沒錢你娶屁!”
騾車緩緩動起來,車上裝滿阿滿家的出産,也載滿了二房的希望和小子娶媳婦的本錢。
不遠處的柳樹下,春桃躲在樹後看騾車走遠,想起男人對自己的保證。
“春桃你等我,這次我一定要掙到錢,一定風光把你娶回家。”文海眼裡滿是鄭重,“我會讓你過上好日子的。”
柳樹後面的野林子,一雙滿是血絲眼睛躲在暗處,握緊的拳頭青筋乍起。
楊家一步步邁入正規,潘氏每天搭阿滿和峥子的馬車去鎮上上工。
楊二舅和文海走的第二天,作坊又重新開工了,村裡人熟悉白色工作服又成了亮麗的風景線。
錢氏每天看的流口水,奈何加入不進去,隻能使勁讨好自己的财神爺,阿滿出去賣東西,二舅母就來幫芳嬸幹活,收拾果子,晾幹菜,地裡除草啥的。
有啥活她幹啥,芳嬸從一開始的不适應到現在的麻木,和阿滿開玩笑說,“你這二舅母都快成咱家人了,一天有大半天在咱家裡。
也不怕你外婆不答應。”
“沒事,我二舅母不笨,指定家裡的活計幹完了,要不然大舅母都不答應。”
芳嬸笑出聲,這妯娌倆天天鬥的像烏眼雞似的,村裡有眼睛都看出來了。
...........
按照往年慣例,每年夏收過後,衙門就會來收夏糧稅,今年都八月五号了,也沒見人來,村裡人議論紛紛。
心裡覺着是不是今年不收了,都存着僥幸心思。
誰知八月五日半下午,村裡人上工的上工,聊閑的聊閑,
村中央的大槐樹下,婦人們聊得火熱。
五六個穿着黑色衙役服飾,腰佩長刀的年輕衙役敲鑼打鼓,進入青松村,身後還跟着十來輛騾車,車上堆着不少糧食袋子。
村裡人一看,還有啥不明白的,這是來收糧稅來了,翠花嬸站起來,笑着迎上去。
“官爺們稍等啊,我這就去喊我家那口子。”
芳嬸也顧不得閑聊,提着針線簍子往家趕,官差們可不會挨家挨戶敲門收糧稅,鑼一響就是提醒村民老老實實拎着糧食出來。